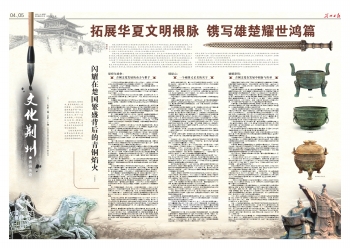|
|||||||||
|
|||||||||
|
编者按 铜绿山漫野的芳草催生了雄楚青铜文化的耀世风华,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隧道,剥离岁月浸染的沧桑青绿,一个让世界瞠目惊叹的文明时代款款走来。它让华夏文明之源更加辽阔恢弘,灿烂的文化巨川倍增熠熠星辉。寒光如雪、吹毛立断的神兵,展示万山之巅的绝世风采;声遏行云、摇动心旌的编钟,演绎泱泱大国的强盛雍容。雄楚青铜,一个一鸣惊人、后来居上的历史佳话,一段让后人热血沸腾、叹为观止的文化宏篇。 青铜,加速了楚国的崛起和繁盛,成就了楚文化的璀璨和厚重。当年,楚人以帝高阳之苗裔自居,周成王时,熊绎立国于楚地,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春秋时期,因为青铜技术的加持,如虎添翼的楚国先后吞并汉淮之间四十余国,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败晋服郑,问鼎中原。雄厚的国力与多元的传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荆州作为是楚国都城之地,楚人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的青铜器,以其富丽纹饰和精湛工艺,展现了楚文化独领风骚、彪炳千秋的魅力。 摆脱了周式铜器传统的束缚,造型新颖、独具特色、形态各异的鼎类,彰显了楚文化的瑰丽雄奇、恣肆浪漫;方壶、圆壶、尊缶及盉等精美绝伦、匠心独具的酒器,再现了楚先人的自由狂放、笑傲江湖的神采;而用于礼仪活动的青铜水器,典雅庄重、浑然天成,草蛇灰线,埋藏与中原文化的血脉相连;锽锽钟鼓,锵锵磬管,如同心灵密码,为解读这段尘封的历史,提供了可以同先贤们对话的同声传译;而杀伤力极强、铸造精良的兵器、车马,为楚国疆域的开拓、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光里,青铜一直是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于觥筹交错、刀光剑影中,长袖翩跹、轻歌曼舞里,书写那一段注定辉煌的青铜传奇。 传承历史,展望未来。文化自信助推城市发展,祖先的荣耀激励后人奋发向上、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勇气。本期文化荆州特聘楚文化研究学者、荆州市社科联学术委员张卫平先生,以缜密之思维、科学之考据、流畅之文笔、奔涌之文思,发掘楚国指点江山背后的青铜风采,抉剔漫漶于冉冉流光之中的神秘铭文,梳理利剑寒光交织“九龙之钟”的壮阔音响中楚国行进的足迹,再现与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青铜焰火和令人血脉偾张的旷世传奇。 落日熔金,残阳如血,肃杀的战场上,寒风猎猎。一位乱发虬髯的侠客手持一柄三尺青铜长剑,身背一支黑色长弓,跨下一匹赤血神驹,一声长啸,纵马狂奔,睥睨天下。这样的画面,恐怕是许多武侠迷们常常幻想的场景。 文献记载和传奇故事让我们看到,在先秦争霸的烽烟中,熊熊燃烧着青铜的焰火。 闪耀在楚国繁盛背后的青铜焰火 □张卫平 祭祀与战争: 青铜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推手 从专家研究成果来看,青铜冶炼是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一;就荆州人的切身感受来说,荆州博物馆里陈列的各式青铜器,生动展现了不一样的楚国传奇! 在商周时期,人们给予了青铜器以极高的地位——谁拥有青铜器,就拥有了与天地沟通的资格,就有资格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在先秦时期是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楚居》记载,熊绎在周初被周成王分封为子爵,带着楚人背井离乡去封地丹阳建国时,为了祭祖不得不带着族人去偷了邻国的一头小牛。 为了祭祖,君主竟然带头去当小偷,可见祭祀之重要。正如《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所说的,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那时无论作战还祭祀,都离不开青铜。 所谓青铜,是指红铜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和吉金,其合金成份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 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青铜制品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最早发明青铜器的西亚,在两河流域曾出土过苏美尔王朝时期的大型铜刀和阿卡德王国时期萨尔贡一世的青铜像。在欧洲,最早出现青铜器身影的是巴尔干半岛东部和爱琴海地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对青铜器的记载:火神赫菲斯托斯把铜、锡等投入熔炉,炼成了阿基琉斯所用的盾牌。 那么,中国的青铜器又起源于什么时代呢?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铜器是出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经分析,成份均为含铜、锌的原始黄铜制品。 1973年11月,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出土了一块铜片,经化验含铜量达65%。这件异常珍贵的文物,将我国的冶金史提前到6700多年以前。不过,那是将铜锌矿石熔化后做出的,并非真正意义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史学家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具体来说,中国青铜文化形成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年;于夏朝进入鼎盛期,历经商、西周和春秋及战国早期;转变期则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 那么,楚人最早使用青铜器又是什么时间呢?史载,周昭王在率兵攻打楚国时,曾缴获了楚人使用的青铜器,而出土文物更是证实了楚地至少在商、周时期就使用了青铜器。1965年,从江陵张家山遗址的商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件铜箭镞、在西周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件鱼钩。1981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沙市周梁玉桥殷商遗址里也出土过铜削刀和鱼钩。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荆州出土的就更多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就是青铜礼器和兵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混战中,青铜制造当然就不能只铸造用于祭祀的礼器了,生产一些更具杀伤力的青铜兵器,就成为了青铜冶铸业最主要的任务。 由于战争需要,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代表青铜文化最高水平的器物当属青铜剑了。考古人员在陕西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等地,都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青铜剑。当时青铜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产量非常小,造价又十分昂贵,只有贵族才能拥有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青铜器。那时,腰间能挂上一把青铜剑那绝对是非常时髦与拉风的了。大诗人屈原曾在诗中非常得意地写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屈原用“陆离”来描写自己所佩带剑饰的样子,就是有力的证明。 尚武,是楚人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楚人在求生存和图发展的艰难历程中筚路蓝缕,成就了尚武精神。爱剑,正是楚人尚武精神的具体体现。于是,在群雄争霸的情况下,楚国的青铜铸剑业迅速发展,铸造的青铜剑更加精细,式样不断增多,数量巨大。 由于战争需要,青铜剑从贵族的玩物逐渐普及到全社会。在荆州考古发掘的楚墓中,只要是男性墓葬,大都有青铜剑随葬。就连江陵望山2号楚墓的女性墓主,竟然也随葬了一把青铜剑。在江陵雨台山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剑,全部都在一椁一棺、单棺和无棺墓中。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楚国平民百姓也已佩剑成风。 当然,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制作兵器的同时,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在荆州出土的青铜器物涵盖面非常广泛。衣食住行,处处都有青铜器不凡的身影。于是,我们在荆州博物馆里看到了大量青铜兵器,看到许多青铜器礼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以生活用具为例,水器有盆、鉴、盘,酒器有卣、壶、尊,蒸煮器有鼎,盛食器有簋、豆、敦,等等。“这些繁多的青铜器物勾画了一幅楚国生活的丰富画卷”。正如文史达人王伟在《楚国简史》一书中写的那样,荆州的“这些出土的铜器,诉说着楚人生活的轨迹以及楚国崛起的历程”。 楚人对青铜非常重视,《史记》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公元前642年,郑国君主郑文公专程到楚国表示臣服,楚成王对郑文公恭恭敬敬的拜见非常满意,得意忘形之际送了1000斤青铜给郑国。本来,此时楚国已是青铜资源大国,1000斤青铜不算什么,但是楚成王担心郑国用这些青铜铸造成兵器来攻打楚国,所以又去找郑文公,直到郑文公再三承诺只用这些青铜铸礼器,才放郑文公回国。 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春秋战国时青铜器大致可以划分为南方、北方两大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在《论青铜文化》中指出,南北两个系统,作风有所不同,器物的种类、形制也有差别,但有很多共同点,如纹饰从过去那种平雕的花纹发展到浮雕式的,甚至出现立体镂空的繁缛装饰;又如流行错金的铭文和镶嵌,使器物呈现出富丽堂皇的外观。跨入战国中期后,青铜器的风格又有一定改变。 简单地说,青铜器的南北差异就是北方器形凝重瑰伟、南方比较浪漫。对此,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的叶培成副研究馆员认为,楚国的青铜器经历了模仿、风格和个性发展三个阶段。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早、中期时铸造的青铜鼎、簋、壶、盘和匜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在形制上基本相同;但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时,楚国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铭文和组合等方面均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到了战国中、晚期,楚国的青铜器有了繁复美观的纹饰,显示出楚器独具个性的特征。 铜绿山: 一个硬朗又柔美的名字 铜绿山,富有诗意的名字。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的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铜绿山虽不怎么高大,但它漫山遍野怒放的紫红小花海州香薷却是楚王眼中的“仙女”! 说海州香薷是仙女的确不为过。话说三四千年前,一次冬天烤火奇遇,让一个药农偶然发现开着紫红小花的地方,有一种神奇的石头,在高温烧烤后竟可做成任意的形状。于是,一把坚硬的“铲子”成了挖药工具。奇异的铜矿就这样被发现!从此,满山海州香薷也被人们称之为铜草花。如今,铜绿山上盛开的铜草花,见证了中国璀璨的青铜文明和楚人创造的青铜传奇! 考古发掘证实,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是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矿冶遗址。 在春秋战国时期,铜矿资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虽然周王朝控制着铜绿山,但鄂南的大冶离南阳盆地毕竟路途遥远,开采出来的铜矿石须经长江然后转入汉江,最后通过随枣走廊抵达周朝首都洛阳。这样一折腾,敏感的楚人很快就嗅到了青铜那独特的味道。 无论是楚国初创时期还是崛起之后,楚人在争霸战中深深体会到了青铜兵器的强大威力,为自己拥有的铜不多而着急。于是,就有了武王三次伐随。 楚人虽然强悍,但最初对铜绿山铜矿却是鞭长莫及。不过,楚人非常聪明,一番琢磨后,武王把主意打到了那漫长的运输线上。先是相继灭了通往铜绿山的好几个国家,最后,才拿国力比自己强的随国开刀。尽管楚军如狼似虎,但是拥有青铜的随国比楚国还要厉害,连续两次,武王亲率大军攻伐随国都战败了。直到16年后的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在年逾古稀之年第三次率军向随国进发,不妙的是,还在路上的武王就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但他渴望着在有生之年为楚国的雄起再拼一次,于是带着病体继续前进。然而,楚武王生命在行军路上走到了尽头。将士们遵照武王临终前的安排,化悲痛为力量,一举攻占随国,将铜绿山划入楚国版图。后来,楚庄王正是因为拥有了中国最大的铜矿带,心中底气十足,才敢在洛河边上检阅楚军,豪情满怀地问鼎中原。 从此,楚国发展一日千里!正如王伟先生在《楚国简史》中写的那样,“铜绿山,一个硬朗又柔美的名字。我们或许觉得陌生,然而对于当时的楚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天与地”。 “在先秦人的眼中,铜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把它铸造成兵器,就相当于给人类插上翅膀一样无所不能。”的确,青铜兵器大量列装楚军,极大地提高了楚国军队的战斗力。 在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对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在这处春秋时期的古矿遗址里竟然有着近40万吨的炉渣。通过对这堆炉渣的推算得知,仅仅这里的产铜量就高达12万吨左右。 12万吨铜对楚人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对此有一个直观的感觉,那就是12万吨铜可以制造成6000万把青铜剑,或2.4亿件青铜戈,或40亿枚青铜箭头。好家伙!这该迸发出多么强大的战力啊!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铜绿山的铜矿资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难怪王伟先生在写作《楚国简史》一书时,竟然用了“楚国崛起的利刃”“一个国家的命脉”“战争的利刃,铜绿山”三个章节,来述说青铜对楚国崛起的重要意义。 正如“核”工业问世后投入战争,美国以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而结束“二战”。其后,核工业才用于发电、医疗等。这看似悖论,其实血雨腥风的战争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催化剂。而荆州人民记忆最深刻的古代青铜器,就是荆州博物馆里收藏的四代越王剑。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2000多年前,吴、楚、越三国铸造的青铜宝剑,就是群雄争霸战中克敌制胜的杀手锏。 国家因战争的胜负而存亡。从冶矿、铸剑开始,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中,中国古代青铜兵器制造工艺与技术已站立到了世界之巅。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里阿诺斯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仍以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最古老的文明而骄傲”。无疑,从荆州出土的大量楚式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里程碑式的实物证据。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脚步要比两河流域的西亚地区晚上三四千年,但却几乎与古埃及同时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不过,令学者大为不解的是,如同当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三级跳一样,中国古代的青铜时期更是以极快的速度跃过了婴儿期,似乎突然之间就超过了美索不达米亚。 古希腊人把文明雕刻在大理石上,中国古人则用青铜写下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文明史。只是,中国青铜文明发展的推手是祭祀与战争。青铜兵器的出现及广泛使用,更给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争夺增添了几分惨烈与残酷。 千百年来,争夺生存资源,帝王的欲望让历史充满着血腥的杀戮。战争,更是催生了青铜兵器的诞生。远古时期,古人削木成剑,将细木棒前端用石块削尖或在石上磨尖,当作刀剑或箭矢,用于作战。这,就是成语“剡木为矢”。 其实,楚国初创时期也是“剡木为矢”的。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时的楚国“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这里的“桃弧”,就是指用桃木所制的弓;“棘矢”,则是用荆条枝磨制成的箭矢。 比较有意思的是,楚国的强势崛起是在楚武王、楚文王父子俩接力完成两件楚国发展史上标志性的大事件以后——武王三次伐随夺得铜绿山铜矿、文王迁都纪南城将扩张的目标放在富裕的江汉平原。 几百年来,居安思危的楚人不停地“战斗、战斗”,力图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了海量青铜资源后,楚人又在公元前333年灭了吴国和越国,并将两国铸剑名师与工匠强掳到楚国。于是,楚人用学到的先进铸剑技术制造了大量锋利的青铜剑,还用青铜“将战车改装得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战士,有着铜墙铁壁,所向无敌”。于是,一个又一个诸侯国被装备先进的楚国收入囊中,用设置“县制”的方式进行管理。 楚国强掳吴越巧工之事,犹如二战后美国大批招揽德国工程师一样,正是在德国工程师的帮助下,美国的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并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楚国也一样,在用武力吞并吴、越后,掌握了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铸剑技术,一跃成为铸剑名地。 在论及楚国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时,著名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曾以“外求诸人而博采众长,内求于已而独创一格”予以概括。正因为如此,才使楚国的青铜器铸造后来居上,成为支撑美仑美奂楚文化高崇邃宇的六大支柱之一。 破解密码: 青铜文化在发展中创新与传承 楚国虽然掌控了铜绿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青铜资源,但青铜毕竟仍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稀缺的战略物资。于是,聪明的楚人就动起了脑筋,一番试验后,仿铜漆礼器便问世了。这件事,体现了楚人“追新逐奇,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也是后世公认的楚文化精髓之一。 在商末周初楚国始立之时,楚人就开始使用青铜器了。但由于生产力低下,青铜器的发展尚未成熟。后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域的扩张,楚国破解了随国、吴国和越国等国先进的青铜铸造技艺,并通过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楚系青铜器。专家认为,在浙川下寺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国铜器,造型独具一格,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其浮雕、镂雕、镶嵌、铸镶等纹饰的工艺制法,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件“国宝”——春秋云纹铜禁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件文物的主人,就是“问鼎中原”楚庄王的儿子楚国令尹子庚。作为在国家首批严禁出境的文物,云纹铜禁是整体用失蜡法铸就的。 所谓失蜡法,就是用蜂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向内浇灌熔液,铸成器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是在唐代初年。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楚国云纹铜禁的出土,证明失蜡法并非舶来品,而是中国固有的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并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由此,学界认为失蜡法铸造工艺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相当成熟。历史学教授黄德馨先生说:楚国“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工艺,生产了大量青铜礼器、武器、工具与生活用具,在战国七雄中,居于先进行列,堪称后来居上,成就惊人”。时时创新的楚国,就这样一跃而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楚人的仿铜漆礼器一直是云里雾里,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难以看到庐山真面目。直到200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从枣阳九连墩发掘的一座大型东周楚墓中,出土一批仿铜漆礼器后,楚人发明的“仿铜漆礼器”工艺才开始明晰了起来。 楚人的仿铜漆礼器类别及形制特征与同时代铜礼器相一致,器形几乎包含所有青铜礼器类型,可分为炊器、盛食器、酒水器、盥洗器等四大类。 楚人掌控了铜绿山,按理说是不缺铜了,但楚人的危机感非常强,他们发明仿铜漆礼器,并不是手里的铜不够用,而是希望在确保祭祀需要的基础上,留出更多的青铜资源用于军事装备工业。 正当青铜剑在战场上大展神威,屡建奇功,尽显风流之时,钢铁制造的兵器悄然登上战争舞台。这个时期的中国钢铁兵器的水准已领先全世界。因此,楚国在发展青铜剑铸造业的同时,也积极铸造钢铁剑。史料中说,楚国铁剑和钢剑的发展引起了各诸侯国极大恐慌。 战国后期,青铜剑仍占据着兵器的主流,在楚国绽放最后的光彩。历史学家杨泓先生说:“钢铁冶锻工艺到战国时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掌握了块炼铁固态渗碳制钢的方法,钢铁兵器较多出现于战争舞台,在当时的燕、楚等国境内,都出土过较多的战国晚期钢铁兵器,标志着青铜兵器衰落的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可见,楚国的青铜兵器和钢铁兵器都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兵器。 两千多年过去了,青铜宝剑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 从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作为“中华第一剑”永远都是荆州人民关注的对象。十几年前的“孪生”神剑之谜,至今还影响着荆州。据媒体报道,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的一位文物鉴定专家,2004年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的地摊上,居然只用1800元就“淘到”了一把越王勾践剑。这件事,当即被“越王勾践剑”的收藏者——湖北省博物馆的专家否了。 就在这件事被炒得纷纷扬扬时,在越王勾践剑的“出生”地荆州,又传出了许光国用14年时间破解越王剑铸造千古之谜的新闻。随后,在越王勾践的家乡杭州与苏州,也都宣布破解了铸造密码,复制、还原了“天下第一剑”。 聪明的荆州人从这些新闻中看到了商机。一石激起千层浪!别人能铸造出高仿真的越王勾践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于是,从本世初开始,一个个青铜剑铸造的手工作坊,在荆州城区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古老的荆楚大地,仿佛又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铜水飞溅,锤声四起,在工匠们的精心铸造下,一柄柄青铜宝剑傲然于世。 一柄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宝剑,还能如此刺激着当代人的神经,正说明了其本身的价值。而众多山寨越王剑的诞生,也以另一种表现方式,继续在热兵器时代展现着冷兵器时代不朽的青铜传奇。 正是由于楚国青铜文化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十多年前曾有国家文物局领导希望荆州能“复制”出“真正”的楚国青铜器,作为国家元首出访国外时赠送的国礼。然而,仿制是一回事,传承又是一回事。破解了铸剑密码,不等于就能真正制造出“楚国”的青铜器。“国礼”自然是没了下文,而在荆州众多的“非遗”传承名单中,荆州最为骄傲的青铜制造与丝绸织造却一直没有能够出现。似乎,当年秦将白起拔郢时一把冲天的大火将楚人所有的传承都烧得精光。 为什么荆州人能破解越王剑铸造的千古之谜,却铸造不出真正的楚国青铜器?其实,这是涉及到“非遗传承”与复制仿制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传承”二字上。套用一句演艺界对某些扮演领袖人物特型演员的评价,就是“形似”与“神似”的区别。 传承,从汉语词语的解释来看,泛指对某种技艺在师徒间的传授和继承的过程。注意,这里说的是“师徒间的传授过程”。许光国、张云们,都是在研究古人铸剑技艺基础上进行反复试验后复制的,并非是用一代又一代通过师傅口口相传的技艺。所以,在专家看来只能是“形似”而不可能达到“神似”。因此,考古学家、湖北省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陈中行先生说,经过比较,不难发现越王勾践剑与“高仿真”剑存在极大差异,两者不具有可比性。看来,复制与仿制,只能达到“形似”;要“神似”,必须靠“传承”。 每一件从荆州大地出土的青铜器、每一件楚国的青铜器都承载着厚重的荆楚文化,都留下了令人惊艳的绝世风采,将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智慧演绎得完美绝伦,既让我们由衷地感叹楚文化的辉煌和气势,也留下了诸多谜团留待我们去探索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