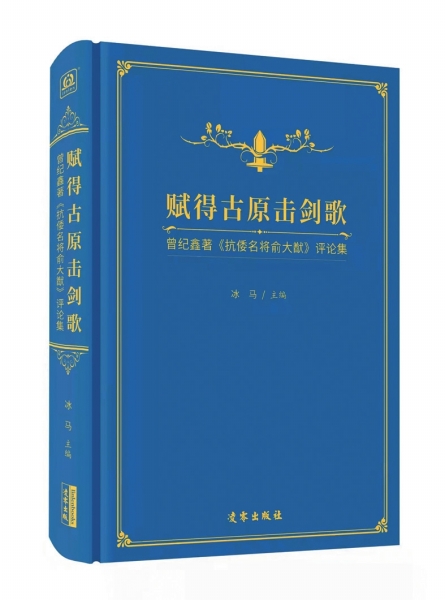|
||||
|
||||
|
□潘清河 曾纪鑫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抗倭名将俞大猷》自2015年9月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大量相关介绍、报道、访谈、论文、评论等纷纷见诸报刊、网络。正是如此众多的评说,催生了《赋得古原击剑歌》一书的问世。书中遴选了38篇学者、作家的评论文章,可谓精彩纷呈,让这本书充满着诱人的芳香。 所谓评论文章,就是对原著进行价值判断后的再创作,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信息交流和情感互动的桥梁。《赋得古原击剑歌》的学术性与价值感,源自于书评人对《抗倭名将俞大猷》的深刻感悟和真知灼见,并与原作者在思想上所产生的共鸣。 《抗倭名将俞大猷》融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历史性、资料性于一体,对了解和研究民族英雄俞大猷的历史功勋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以“还原历史,回归真相”为立足点,用丰富殷实的史料、生动细腻的文笔、独到新颖的见解,讲述了俞大猷的生命历程与不朽功勋。马卡丹在《眼光·胆识·热情》一文中写道:“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不仅要求作者有对那个阶段历史的深刻认知,有对所传人物的精确把握,更要有常人往往不曾具备的独到眼光,能够洞穿历史烟云的重重遮蔽,发现人所未知或是已知却有意无意间忽略的真相。……纪鑫先生这部俞大猷传,把独到的眼光、独具的胆识、由衷的热情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引领读者一步步走进历史的烟云,走进那个颇具争议却是魅力非凡的人物的内心。”朱丹林在《浅议<抗倭名将俞大猷>》中这样评价道:“作者曾纪鑫先生的知识结构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有历史学方面的根底,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比较深刻,他的文化视野也非常宽阔并且具有穿透性。”诚然,曾纪鑫的独具慧眼,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相,看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俞大猷。 评论集锦《赋得古原击剑歌》,无疑扩大了《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影响力,让俞大猷的事迹与精神感染更多的读者,也让读者能够走进俞大猷的心灵世界。纵览书中所选38篇评论作品,或学术论文,或书评,或随笔札记,或读后感,皆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评价《抗倭名将俞大猷》,对原著的精神内涵、艺术成就等予以提炼、升华、拓展,让读者对俞大猷的文韬武略、人格魅力有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认知,从而起到一种辅助阅读的功效。 众所周知,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始终是曾纪鑫文艺创作的初心与使命。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历史人物传记等一系列书籍,注重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尤其在如何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等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还原历史,回归真相”,也是《抗倭名将俞大猷》一书的最大亮点和看点,更是不少学者对该书评论的要点。又见小寒在《真英雄,俞大猷》中坦言:“想要真正认识一个人,要从谈吐感知思想,从行为探究内心,从原生家庭解析人生际遇。为了还世人一个真实的俞大猷,曾纪鑫以史实为鉴,穿过了五百年的时空:他研读俞大猷所著《正气堂全集》,与俞大猷进行心灵的对话;他走过俞大猷奋斗的足迹,感受他的热血精神;他通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与俞大猷有关的资料,不仅研究他的生平,还研究与他同时期的戚继光、谭纶等名将;不仅研究明史,还研究倭寇史、贸易史、中日关系史;他多方考证,严谨思索,还原现场,辨明真相,《抗倭名将俞大猷》处处透出一个‘真’字。”彭晓玲在《一支史笔写春秋》中写道:“纵观全书,作者始终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未被某种情绪、某一观点所左右,清醒而又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俞大猷以公正的历史地位。”是啊,求真务实是做人的底色,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曾纪鑫以他的求真精神,拨开历史的浓雾,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也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历史或许会沉默,但从不说谎,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曾纪鑫在他众多的历史题材的专著里,无一例外地把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真实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一如既往地守护着道德良知的底线。只有发自肺腑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的内心,才能深得读者的青睐和追捧。然而,要从陈旧的历史往事、枯燥的历史资料中求证、求真,写出生动的历史故事,甚至把历史人物盘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树德在《斩鲸碧海颂英雄》中由衷感慨:“作者把陈旧的历史资料从古板、枯燥的文献,演化成了生机勃勃的历史故事,赋予历史以生命力,也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芒。”冰马在《历史人物传记的主观性、客观性与表现力初探》中认为:“历史人物传记书写的根基是,书写者首先必须扎牢‘历史科学’的学术意识,在书写和建构人物的形象空间过程中,坚守对‘过去的事实’的文献档案、证据文本等史料的挖掘、梳理、考辨、阐释等‘冷板凳’的功夫。” 常言道:“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为了实事求是地再现历史真相,曾纪鑫坐过的冷板凳,又何止10年、20年、30年…… 历史散文在文学体裁中最难着笔,因为它是以记述历史事件演化过程为主的文体,不像小说那样可以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必须记录真实的人和事。但历史散文如果写得太直白、太理性,又会失去文章的生动性。曾纪鑫是一位集文学、历史、哲学于一体的著名作家,作家写历史,自然比历史学家写历史更有生动性和可读性,至少在人物刻画方面更为灵动,更有血肉。冰马在《历史人物传记的主观性、客观性与表现力初探》中证实了作者的笔法:“本文在此强调的是传记体写作的非虚构——虚构之间存在的张力问题与平衡性问题,如果一味地强调史事考据、辩证,则将沦为学术论文式的穷究与思辨;如果过于突出人物的塑造、故事的建构、情节的编排,必将沦为历史小说式杜撰与虚拟甚至‘戏说’。”孙永庆在《还原历史遮蔽人物的写作探索》中也特别指出:“《抗倭名将俞大猷》为历史‘去蔽’,作者‘用小说式的文字’写历史人物,写活了这位抗倭英雄;同时描绘出他所处的社会时代风貌,在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让历史叙事蕴含客观、公允、公正的史德与史观,也为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写作范例。” “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春秋。”曾纪鑫不仅是一位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型作家,也是一位有良知、敢直言的作家。他站在历史的岸边,为正义发声,通过他的笔、他的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体现出一种难得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正如沈世豪在《真实是伟大的力量》一文中所言:“历史是公正的。此话的含义除了说明历史经得起无情岁月的检验之外,还有一层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内容,这就是昭示人们不能满足于现成典籍和俗世的见解,要负责地勇于揭开层层的迷雾,回归历史真实的本来面貌,使几乎远去的历史,抖落一身风尘,重新站在人们面前。这是后人的责任,更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天职。”也如莫非所说:“记录封建王朝时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深入他的经历与思想,挖掘思考其人生意义的发展过程,作者显然是要用民族史诗的重述,传达一种不随时间而改变的坚定力量,一种永恒的精神和普世的价值。这,也正是历史与文学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之所在。”(《责任与使命:在历史与文学之间》) 在《赋得古原击剑歌》这部评论集里,众多文化学者对《抗倭名将俞大猷》的精彩评论,足以让我们感同身受、深受启迪。让读者不仅看到一个真实的俞大猷,同时也看到一个真实的曾纪鑫,看到了作者为本书创作所付出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