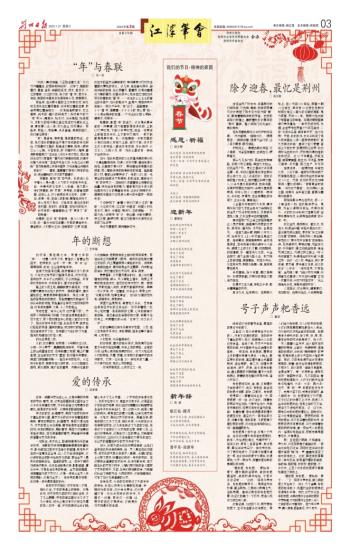|
||||
|
□戴军 说到记忆中的春节食品,最难忘的莫过于糍粑了。 上世纪70年代或更早生于农村的人,没有不记得糍粑的。在物质并不富裕的那个年代,糍粑是大众化的过年食品。每到冬季,家家户户杵糍粑的时候,村子里就开始流淌糯米的香味。一般来说,杵糍粑前,需要将上好的糯米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甚至更长的时间,直至糯米看上去晶莹剔透,洁白亮眼。第二天,将糯米捞出淘洗、滤干、沥净,连水装进饭甑后,盖上圆圆的木制锅盖,置于大灶的铁锅上,接着就在灶膛内支起木柴,猛火燃烧了。 杵糍粑讲究快、准、稳,这样糯米才能杵得均匀、瓷实,有韧性,做出来的糍粑才细腻、柔软,口感好。杵糍粑一般是四个人围着石臼各站一方,四根粑棍一按一扯,依次往返。随着杵的频率开始加快,力度开始加大,先前有节奏的按、压要逐渐变成猛烈的捅、捣!杵着杵着,原本饱满圆润的糯米被碾压成粉,直至成为一团纯白的云泥,如膏似脂,绵软柔韧,几根粑棒交错拉起的刹那,还会扯出细细的白丝,如一道道耀眼的光。 杵糍粑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力气活。当石臼内糯米牢牢黏住粑棍时,就有人开始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了。每到这时,便有人自告奋勇,接过粑棍,围绕石臼走马灯一样边走边杵。为了更好地使力,不将棍子和糯米缠在一起,他们手中的棍子下得快,收得更快,大家一鼓作气,向着糍粑将熟的高潮阶段冲刺。 “揣糍粑、杵糍粑,一棍挨到一棍下,糯米揣的活团哒,做的糍粑圆溜哒,婆婆吃得笑哈哈,不把爹爹忘记哒……”这时,一阵号子声传来。杵糍粑时喊号子,一是保证动作协调,配合默契;二是可以鼓舞士气,活跃氛围。看到这熟悉的杵糍粑场景,我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思绪从现实又被拉到从前。 依稀记得,儿时的冬天,哪家要杵糍粑了,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男人们出力杵糍粑,女人们协助按糍粑,小孩们则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身后,只为抢吃还没完全做好的糍粑。糍粑是有多种吃法的,除了煎、炸、煮、蒸,最有印象的吃法就是烤了。除夕夜,一家人围着火盆守岁,当火钳支在燃着的树蔸旁,上面放一块硬梆梆、湿漉漉的糍粑时,会听到“噗哧噗哧”的声响,那是糍粑上的水气落到火堆的声音。起初,它的身体遇热后会变得软塌塌的,接着,就开始变得胀鼓鼓的。不用多久,向火的那一面就外焦里嫩,金黄金黄了。等一边烤熟后,得赶紧将另一面翻转过来。几次来回后,看到糍粑越撑越大,小孩子们就开始猴急似地催叫:大点!大点!再大点!突然,“嘭”的一声,糍粑的肚皮炸开了。或是兴奋不已,或是受到惊吓,拿火钳的手一抖,糍粑掉在了灰烬里。孩子们这时会顾不上烫手,迅速从火盆中将糍粑抢出,在身上拍打几下后,便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这一口下去,顿觉口中的糍粑软糯拉丝,回味悠长,至今还是唇齿留香。想想那时候,烤完糍粑后,还不忘沿着糍粑的边缘,将鼓鼓的表皮有意挑破,只为伴随着糍粑的吱吱作响,看一股白气从糍粑肚内一溜烟似地钻出来,那感觉真是惬意无比,妙趣横生。 起!正在回忆期间,不知道谁一声大叫,只见四根棒子直插臼底,一团白光倏地闪过后,刚刚还在石臼内的糯米面团“啪”地一声,重重地落在了旁边的案板上。这时,围在案板周围的人争先恐后,揪起温热糯软的面团,拍的拍,捏的捏,拧的拧,搓的搓,不一会功夫,上百个成形的糍粑便齐刷刷地铺在了案板上。 “揣糍粑、杵糍粑,一棍挨到一棍下……”又一阵号子声传来,第二锅糍粑又开始杵了。如今,为了省事,杵糍粑的越来越少,机器打出的糍粑早已变得稀松平常。可我,依然怀念当年的糍粑,与其说是怀念当年糍粑的芬芳味道,不如说是怀念当年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友善纯朴。因为号子声声、情义绵绵,粑香虽远、岁久弥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