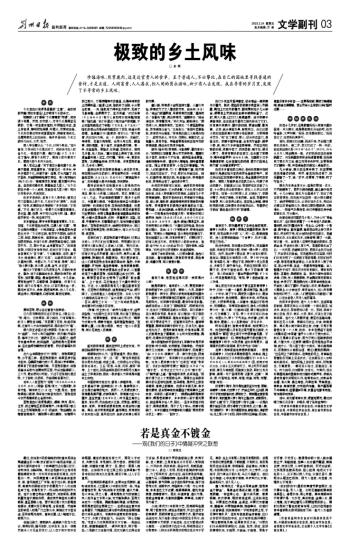|
||||
|
□安频 珍馐海味、熊掌鹿肉,这是达官贵人的食单。至于普通人,不必攀比,在自己的园地里寻找普通的食材,才是正道。人间富贵,人人渴求,但人间的隽永滋味,却少有人去发现。我在寻常的岁月里,发现了不寻常的乡土风味。 冬瓜 冬瓜自古以来便是吾国的“土著”。连权威的药籍《神农本草经》上亦载有冬瓜的条文。 城镇的人们“邂逅”冬瓜藤蔓的“际遇”,或许很少有罢。然而,农村的人,对于冬瓜是司空见惯的。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叶柄粗壮中空,茎上有卷须,藤叶附地伸展,叶肥大,花黄或白色。冬瓜形状接近球形或者圆柱形,表面有细绒毛,经霜则青皮上白如涂粉。俺爹爹告诉我,冬瓜又被呼为白瓜、水芝、地芝。 明人李东璧氏云:“冬瓜,以其冬熟也。”如今看来,冬季采收冬瓜是忒迟了。或许由于古人贮备冬瓜,一般在初冬罢。俺们乡曲(方言,乡间)过了端午,便有冬瓜吃了。嫩而小的叫青皮冬瓜。肥而大的冬瓜叫大白瓜。 清人笔记上道:“天下结实大者无若冬瓜,味虽不甚佳,而性温可食。”我曾见过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冬瓜,你信不信?但是,它太沉重了,挑不回去,只能眼睁睁地等它溃烂。宋人郑安晓氏《咏冬瓜》云:“翦翦黄花秋复春,霜皮露叶护长生。生来笼统君休笑,腹里能容几百人。”大冬瓜的肚子装一个人尚可,怎能容纳几百人呢?郑氏以夸张手法,极言其巨。 我爹爹告诉我,他有个友人是华侨,曾见过苏门答腊岛上的冬瓜,久放亦不会“腐败”。我诘问:“可是,贮藏的秘法是啥呢?”爹爹却说:“不知道。”不过,俺们这儿一般把冬瓜放置在高燥处,忌近盐、醋、扫帚,并不可以让鸡犬啄、撞。最好和芥籽放一块,可经年不坏。 爹爹曾指出,果子中籽繁富者有夏瓜、冬瓜、石榴。冬瓜籽在肚内成列,江湖人称“瓜犀”。某女士向我透露过一个悦泽面容、令肤色柔软光洁的土方子:“冬瓜籽五两,桃花干片四两,白杨皮二两,剉碎,再研成末。每餐饭后,泡水吞服。倘如想皮肤白,多加冬瓜籽;假使想面容绯红,加桃花干片。三、四十天后,全身都变白了。”我将信将疑,只因没有亲身尝试,故而不好下结论。嗜食者谓瓜为“百子甕”。冬瓜瓤绵软、凉爽,富于水分,味道清淡,谓之“瓜练”。白虚润泽如絮,可以濯洗衣裳。中医认为,冬瓜“味甘,微寒”,可以“除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渴、益气、补五脏”。 俺们乡下的腌冬瓜片很有名气,只怕你未尝过。制法:将冬瓜瓤剖成长条,再掺杂进芥粉、胡芹粉,加好醋、碘盐,最后密封进坛。十几日后,便可取出吃了,口感酸辣,劲道醇香。还有冬瓜蜜片:将冬瓜片焯水,放冷;以石灰沸水治一夜,再滗去石灰水,洗净;再把蜜熬熟,放入冬瓜片,倾出待冷,用磁罐装,口感甘美,酥而无腻味。 豆豉 提到豆豉,想必各位看官大抵熟悉。 汉代的刘熙载探究过它的别名。《释名》云:“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齐人谓豉音如嗜。”菜里羼了豆豉,味道很鲜美,这样齐人才会欢快地吃菜,因此称它为“嗜”。 明代的王志坚氏在《表异录·饮食》中,称它为“幽菽”。为什么叫它幽菽呢?杨升庵《丹铅杂录·解字之妙》云:“盖菽本豆也,以盐配之,幽闭于瓮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幽菽就是大豆煮熟后,经过幽闭发酵而成的意思。杨氏的解释比较合理。 近代台湾同胞称它为“荫豉”。荫豉即黑豆豉,分干湿二种。湿豆豉的制法:将黑豆渍于盐水缸中,经曝晒发酵约两个月,再加以烹煮调味,便具有了较佳的甘醇风味。干豆豉的制法:将制造酱油后的残渣羼到黑豆里,然后加盐曝晒二、三个月,最后便可以吃啦。不过干豆豉相比湿豆豉,少了香味,还很咸。然而酒醉者喜欢它。 日本人人称豆豉为“纳豉”(因为他们以纳豆为原料,故称)。《楚辞·招魂》有之:“大苦咸酸,辛甘行些。”南宋朱文公(熹)注:“大苦,豉也。言取豉调和以椒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豆豉在而今依然是荤菜的必备的作料。 豆豉自古以来便是湖北、湖南、贵州、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区的民间特产。《本草纲目》卷二十五上引用陶隐居(弘景)的话说:“豉出襄阳、钱塘者香美而浓。”襄阳即今湖北襄阳。钱塘即今 浙江杭州。它是馈赠亲友的佳品,也是拌凉菜的上选调味品。《世语》上说,陆机到了洛阳,十分思念故园。一天,陆机进了侍中王济的家,见到了几斛羊酪,他便愕然了。王济笑道:“你们华亭(今上海松江县)有什么食物可以和羊酪相媲美?”陆机道:“我们千里这个地方出产的莼羹,不必放盐豉就胜过了羊酪(千里莼羹,未下盐豉)!”陆机的潜台词是倘使莼羹里放了豆豉,味道会更佳哩。皇清董以宁《踏青游·南村》云:“郭外青青,风日如今方美。觅一个、板桥娘子。向前村,寻诗思。见宿水鸬鹚起。白荡小舟三四。晒鱼蓑、绿杨烟里。有个渔家,将鱼换酒村肆。煮一半,放些盐豉。更指点,松楸道,百年休计。南岗几多墓,无人扫矣。”董氏在船上弄到了鱼,放到酒舍里叫别人加工,还叮嘱:“煮到一半,莫忘放豆豉。”此词静谧安详,村风扑面。没有豆豉的鱼汤,几乎没人要吃。 品质优良的东西素来是商人追逐的对象。早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便有商贾运来一千瓶酒曲和豆豉(出自《史记·货殖列传》)“糵麯盐豉千合”,放到通都大邑中去销售,获利颇丰。 最早记录域外豆豉制法传入的是张茂先(华),他在《博物志》中说:“外国有豉法,以苦酒溲豆,暴(曝)令极燥,以麻油蒸。蒸讫,复暴三过(遍),乃止。然后细捣椒屑晒下,随多少合投之。中国谓之康伯。”中国自古相传至今的制法如何呢?我询问过母亲,母亲说的是俚语。我把这些话整理成书面语:“豆豉是以黑豆或者黄豆为主要原料,利用毛霉曲霉或者细菌蛋白质的作用,分解大豆蛋白质,达到一定程度时,加盐、加酒、干燥等方法,抑制霉的活力,延缓发酵过程而制成。”豆豉的种类较多,倘使按照原料分,可以分为黄豆豉黑豆豉;按照口味分,可以分为淡豆豉、咸豆豉。 母亲还说了,装豆豉的罐子要密封,切莫让水进入,不然它们会发霉变质。贾思勰氏在《齐民要术》里也是这么告诫人们的。贾氏还说:“豆豉功效有和胃、除烦、解腥毒、去寒热。”豆豉还可以疗治风热感冒、怕冷发热、寒热头痛、鼻塞喷嚏、腹痛吐泻、胸里满闷。现代医学研究,让人们得知豆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多种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等。当年抗美援朝,总后勤部为了促进志愿军战士的食欲,从祖国运来了大量的豆豉,加到菜里让战士们吃。最后,精神百倍的战士赶走了凶悍的“联合国军”。上个世纪,马王堆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不过,令人惊异的是有几个器皿里装有豆豉。这豆豉还是黑色的,但是接触空气后,便坏掉了。这说明墓主人也嗜爱豆豉。日本人元开《大唐和尚东征传》云:“备办海粮,红绿米,苓脂一百石,甜豉三十石……”这个和尚就是鉴真。他却喜欢吃放糖多的豆豉。 《豫章·列士传》云:“羊茂为东郡太守,出界卖盐豉。”大抵因为工资不足用,所以背了豆豉出界去卖。可谓清廉者。谢承《后汉书》云:“韩崇为汝南太守,遗妻子粗饭,惟菜茹盐豉而已。”在韩崇心里,公私是分明的。透过一粒小小的豆豉,可以见到古人的清德。 荞麦 监利的荞麦酒,据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然而您晓得荞麦为什么叫荞麦么? 明朝李时珍认为:“茎弱而翘然,易长易收,磨面如麦,故曰:‘荞’,曰:‘荍’。”野生荞麦的茎委实是有点扭曲,或者上翘。它的得名与它原始的形态有关。又名“荍麦、乌麦、花荞、甜荞”等等。上个世纪,陕西省咸阳县杨家湾四号汉墓中出土了荞麦实物,因此一般学者认为荞麦是中国本土作物。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有人种植荞麦。一般立秋前后下种,密种就实(籽)多,稀种则实少。这也是它奇特的地方。阴历八、九月便成熟了。荞麦最畏惧严霜,迟种则减产。荞麦高约五六十厘米,茎空而直(茎略带红色),叶子呈三角状心脏形,有长柄;花白色或淡红色,很繁密;瘦果三角形,有棱。荞麦籽被硬壳包裹,去壳后可以磨面。其实,由于荞麦壳坚硬,富有弹性,荞麦壳可以包到枕头里,通风性优良,能够达到清心明目 的效果。 唐以前,荞麦很少出现在诗文里。从唐代开始,荞麦成为了文人描述的对象。白乐天(居易)云:“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温庭筠云:“日暮鸟飞散,满山荞麦花。”储嗣宗云:“田翁独归去,荞麦露花深。”宋代开始,戴敏诗云:“颇动诗人兴,满园荞麦花。”王质云:“冬青匝路野蜂乱,荞麦满园山雀飞。”王禹称云:“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荞麦是我国三大蜜源作物之一,甜荞花朵大、开花多、花期长,蜜腺发达,泌蜜量大,具有芬香。养蜂者要是来到正在开花的荞麦田里,保证会收获很多蜂蜜。 南宋·陆务观《荞麦熟,刈者满野,喜而有作》云:“城南城北如铺雪,原头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压油油更香,油新饼美争先尝。猎归炽火燎雉兔,相呼值酒喜欲狂。陌上行歌忘恶岁,小妇红妆穗簪髻。”先前,人们收割荞麦,勾(弯)腰用镰刀割,既然费力,而且效率低下。不过,那时也只能如此。而今,收割荞麦,喊来农机,叫他推过去,荞麦秸秆粉碎,荞麦籽出来了,省却很多劳力。 去壳的荞麦籽可以做饭。倘使把荞麦籽磨成粉,再做成面条,它会很滑腻,不会比麦子做的面条差,日本人特别喜欢吃荞麦面,全国有几千家荞麦面馆呢。医学家告诉我们,荞麦面对于高血压、冠心病、糖料病、癌症等等疾病有神奇的改善作用。荞麦里特有的硒是防癌抗癌的主力军。要知道,人体倘如缺硒,会导致很多器官机能失调——它可是食物中的宝贝呀!荞麦粉还可以做煎饼、烧饼(《鉴诫录》有记载:左街沙门怀宝进荞麦烧饼、米饼等等。)皇宋·胡铨《夏旱至秋,田家种荞麦以补岁事》云:“千里还经赤地连,老农作苦也堪怜。来牟(麦子)不复歌丰岁,荞麦犹能救歉年。”荞麦比小麦耐寒瘠,在小麦枯死的情况下,老农指望不上小麦,只有种荞麦了。只要收获了,总可以度过灾年。荞麦是穷人的救命粮食。皇明·徐子先(光启)《农政全书》云:“苗叶煮熟,油盐调食。”我吃过炒过荞麦嫩叶,味道很甜美。 而到了丰收的时候,人们便会酿酒,自古以来如此。譬如程集镇人酿制的荞麦酒,酒色清澈,适量饮用,可以强骨补髓。 菜蕻子 每到冬季,老百姓经常买的一种菜是什么呢? 就是菜蕻子。每年的七、八月,要把菜蕻子的种籽播下去,让它生芽。等到八、九月,菜蕻子的秧苗有一筷子长,便可以移栽到宽阔的地里去了。每株之间要间隔相应的距离,让它们拥抱充足的阳光。长菜蕻子的田里,最怕牛羊来践踏。倘使田的主人见到了“罪魁祸首”,即便是好性子,也免不了要跳起来破口大骂的。因为菜蕻子在冷清的季节里,是俏货,可以增加一笔不菲的收入呢。只要是蔬菜,难免会有害虫“冒犯”。这时,可不要讲客气了。您直接买来药水,灌到喷雾器里,再喷到菜蕻子的叶子上,不消几天,害虫全死光光了。若是叶面有角斑,叶背有白霉,那么这就是发生了霜霉病,小心叶片变成褐色,再枯死,还得去买对症的农药。 而今的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菜蕻子本是芥菜的变种,叶子深裂,边缘皱缩,花鲜黄色。然而菜蕻子又分两种,一种为青色的菜蕻子,民间谓之“白(方言音剥)菜蕻子”;另一种为紫红色,民间谓之“红菜蕻子”。紫菜蕻子比白菜蕻子受欢迎呢。还有人把菜蕻子称为“红菜苔”或者“紫菜苔”。我们乡间的野老谓之“雪里红(或作蕻)”与“春不老”。我考证过它为什么又叫“春不老”。《广群芳谱》上道:“雪深诸菜冻损,此菜独盛。”因而它得了这么个亮丽的名字。刚刚长出来的菜蕻子的长茎质地脆嫩,色泽明艳,是市场上的抢手蔬菜,宴席上的美味。我的爹爹前几年,身子骨还硬朗,总会起早床去田里掐了嫩菜蕻子上街去卖。买菜的人都买精了,一摸便晓得哪是嫩菜蕻子,哪是老菜蕻子。爹爹卖菜从来不漫天要价,而且常常多给人家,因此,一旦爹爹的担子挑来了,常常被围满。用不了几个钟头,菜蕻子脱销了。爹爹挑着担子哼着样板戏唱腔“要像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回家了。 我们乡间正月招待春客,总会端出一碗菜蕻子炒腊肉。制法:把掐好的菜蕻子嫩茎倒入热锅里,再加上切成片的腊肉,翻来覆去地炒几分钟后,便要淋上芝麻油和生姜末等调味品了。这时,调大火苗,让它们入味最重要。由于菜蕻子清香绵软,往往在消灭腊肉之前先抢光了它们。还有清炒菜蕻子,翻炒的时候,要滴白醋、撒鸡精。这样,就会清香扑鼻,鲜嫩爽口。我们这里小菜饭馆里的清炒菜蕻子是招牌菜。只要师傅手艺好,“钩”住了顾客,那么,总会宾客盈门,酒香浮动。菜蕻子营养丰富,含有抗坏血酸、胡萝卜素、铁、钙以及多种维生素等等。然而正月收束的时候,菜蕻子老了,肉质柔韧,嚼不烂,便没人要了。假使有勤快的庄稼汉,他会割了菜蕻子,喂牛或者罗罗(猪的别名)去。如若那个汉子是懒惰的呢,他会在犁地的时候,把它们压到土块下面“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的爹爹曾在武汉待过,告诉我菜蕻子在封建时代是湖北地方官员进贡给皇帝的特产。武汉洪山地区的菜蕻子更有名,是全国最好吃的菜蕻子。黄陂人黎菩萨自幼在武汉长大,吃惯了洪山菜蕻子。民国建立以后,黎菩萨在北京做了大官,十分想念洪山的菜蕻子,便托人从洪山买很多带来。可是一天只吃那么点,时间长了,菜蕻子蔫了,失却了鲜味,只有扔掉。后来,黎菩萨突发奇想,叫人运来洪山的土,在空地上种植,等到收获的时候,口味根本没法和洪山比。黎菩萨这才明白“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辣萝 卜 每到初冬,菜场里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辣萝卜亦很多。辣萝卜即是红而圆的那种,剥开厚皮,可见白嫩多汁的“心”,咬一口,微辣而脆爽。古人王旻早就指出:“冬食萝卜,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 我过去种田,有时偶尔忘却带水,而且唇焦舌敝,走到自家菜园子里,寻到一棵大萝卜,便拔起来。当然,拔出萝卜带出泥,萝卜尚有长根须,直而白,周匝生长细微的小根。萝卜叶子长而绿,有细柔毛,可一把扯下来,擦拭萝卜皮上的湿土,多擦几下,擦干净为止。然而红皮较厚,可以撕下皮,皮并不粘住白肉,是乡下的解渴“神物”。宋人杨诚斋云:“雪白芦菔非芦菔(萝卜别名),吃来自是辣底玉。”可知,萝卜自古白皙,受人欢迎。 细心的妇女还会洗净了带红茎的青绿萝卜叶子,切成一小截一小截的,撒点梅花盐,腌上那么一个中午,到了下午,再使劲儿捏去水分,最后放油锅中炒,色如翡翠。据我爹爹讲,兵燹战乱之时,乡民李师逃难,入石窟中,强盗们不敢进去,用烟薰他。李师因缺氧快死,挣扎之际摸得萝卜叶一束,不顾一切塞到口里,咽下嚼出的绿汁,终于清醒了。可见,萝卜汁液还可以救命哟。中医认为,萝卜“下气消谷、去痰癖、止咳、利膈、宽中、肥健人、令人肌肤细白”,好处多多。 吃到口里时,脆嫩中带微咸,却使胃口大开。我在城市里从没有见过餐厅里有这碗菜,大抵是因为“鄙陋”的土菜不为市民所重视罢。不过,田家偏爱这一口,特别是出劳力的壮健汉子,嚼着腌萝卜叶子,兴致很高,话比平常更多。但是隔夜的便只有倒掉,因为夜气会“夺味”。 泡萝卜是早餐店免费提供的腌菜。一般是买来辣萝卜,切成有点厚度的圆片,洗净后,腌上几天,再泡到加了小米椒的白醋坛子(白醋与水的比例是1:5,圆筒状的玻璃罐子)里,时间不可以太长,十到十五天便可吃了。早上吃热干面的时候,搛几片到碗里,既脆辣又韧劲,同时又有点酸味,套用一句广告词即是“这酸爽,过瘾”!其实,根、叶皆可生、可熟、可葅、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饭…… 还有萝卜阿子,阿子是地道的监利方言,即瓣。将辣萝卜洗净,切成萝卜丁,然后让风吹、让光晒,阿子终于变成皱缩状时,便可收了。特别需注意的是野狗子,有时直接从萝卜阿子上踏过去,迸散四处;有时“心情”好了,干脆在萝卜阿子上睡——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恨不得刳了它的狗皮,这个害人精,专门搞破坏!萝卜阿子最服麻油,醇香绵长、清韵萦绕,泡上那么半个时辰,再拌点四川豆瓣酱,那滋味,简直没有法子形容——主要是甘甜,同时又嚼得脆响,麻油滋润咽喉。想必热爱乡土菜的伙伴们皆吃过罢…… 神仙南瓜汤 我在十几岁时,经常跟着妈妈从菜园子里拎回来一只大南瓜,说是要做南瓜汤给我吃,我欢呼雀跃,大声叫喊:“妈妈,我来帮你的忙。”妈妈答应了,还表扬我真乖巧。 首先,把南瓜切成瓤,再洗干净,然后捏刀把南瓜皮削去。第二步,把它切成了一块一块的,而且抓出南瓜籽(种子称“南瓜子”,供炒吃、榨油或药用),随后再洗一遍。这时妈妈已经放油到锅里了。只见锅里的菜籽油烧得冒青烟,妈妈倒进了南瓜片之后,就立刻用手去铲动,主要是怕它们糊到一起,并在适当的时候加入适当的水。 几分钟后,南瓜已经煮半熟了,我正要喊妈妈来看的时候。突然,看见妈妈过来了,妈妈翻看了一下,说:“孩子,还要煮,不煮熟,吃了坏肚子。” 南瓜片本身含有水分,但是还要加一点水,不然就糊焦了。把热水倒进锅里,盖上盖子继续煮。十几分钟后,南瓜片也湿润多了,变成了纯正的桔黄色,妈妈就开始盛起一部分南瓜糊浆了。倘使要喝南瓜汤,必须还加多点水,炖成远近闻名的神仙南瓜汤,喝到口里软糯甜润,滋味绵长。一阵香气扑鼻而来,我们尝着自己亲手做的南瓜汤,万分高兴。 我曾经问过村里的几个老人,为什么叫“神仙南瓜汤”,他们向我披露了一个失传已久的故事。据说呀,我们村里过去有一片土山,山中有一个老道,惯于辟谷,鹤发童颜,每年在山坡上种了很多南瓜,吃也吃不完,还分给附近的穷庄稼汉。老道煮南瓜汤,水比南瓜片多,滋味奇特,喝了一大碗,可以管一天。后来有人经常吃老道送的南瓜,百病全消,干活亦比别人有力气。老道的南瓜出了名!一天夜里,老道喊来村长,把南瓜全托付给他了,然后羽化而登仙。在老道常住的石室里,村民们只有发现了一双破敝不堪的草鞋,村民们恍然大悟,原来老道是活神仙,从此有很多人搬了进来,在山中开荒、生活,一般都是寿登耄耋。后人整理法子如下:南瓜浓汤材料有南瓜。调料有肉桂粉、豆蔻粉、黑胡椒粉、盐。制法为首先将南瓜洗净,切块,放入蒸锅蒸熟,然后再将蒸好的南瓜取出,去皮切丁,再在锅内放入菜籽油或色拉油,然后放入南瓜丁翻炒,然后加入滚汤,煮沸后转小火再煮上20分钟左右,煮好后关火,加入所有调料就可以吃了。从此,人们便在南瓜汤前冠以“神仙”,以纪念他老人家对人世的福泽。 我的爹爹告诉我,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难的时候,常常在早上从田间搬一个南瓜回来,加点米,煮成汤,那样便可以混一天。那时,菜园子种上豆角、茄子、窝瓜、大葱、黄瓜,还有土豆子和向日葵。当代文人陈振家道,青豆初生雏鸟嘴,南瓜已见小儿拳。嫩南瓜切成丝,炒食,味美滑腴。窝瓜是乡间对南瓜的土称,你看,它是不是蒂芭处有一个小窝,故称。爹爹在遗留下来的《问君日记》中写道“售予乡公所乡丁两大饭瓜。”饭瓜又是南瓜的俗称,因为它可以在缺粮的时候,代替大米。《红楼梦》第四十回刘姥姥出尽洋相,说什么:“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倭瓜就是南瓜,那是别处乡间的俗语。萧红《朦胧的期待》:“已经爬上了架的倭瓜,在黄色的花上,有蜜蜂在带着粉的花瓣上来来去去。”这说明东北人亦呼南瓜做倭瓜。植物图鉴上告诉我,南瓜,附地蔓生,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馀丈,茎粗而空,有毛。叶大而绿,状如蜀葵,亦有毛。开黄花,结实形横圆而扁或圆筒形或纺锤形或葫芦形,表面光滑或有瘤状突起和纵沟,色黄有白纹,成熟后有白霜,有淡黄、橘红等色,肉厚色黄,界面微凹。煮熟食,味面而腻,亦可和肉作羹。原产墨西哥及中南美洲,性喜温暖干燥,我国各地都有栽培,可作蔬菜或饲料。 如今,到处都有南瓜卖,便宜地要死,最近你喝了南瓜汤没有?多喝点,喝了延年益寿哟!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