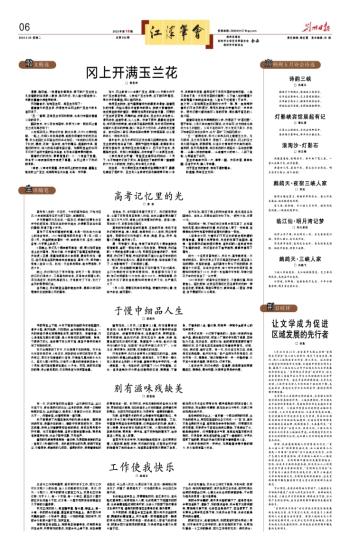|
||||
|
□梁雪瑞 有一次,我在茶馆的阳台看到一盆残缺的花盆,盆口参差不齐,像连绵起伏的山丘;盆身的裂痕,则像一条蜿蜒崎岖的巨龙;盆底的豁口,就像老人背着石头行走,脚印深浅不一。远看奇怪,近看却别有一番风景。 我不禁想起了我国古建筑中的残缺沧桑美。圆明园被破坏后,像重伤后的病人,躺卧中欣赏日起东方。西安古城墙,砖块上刻着鞭策和击穿的痕迹,像城主用身躯守护家园。龙门石窟的佛群,经历千百年世事沧桑,更像是在废墟中修炼,沐浴夕阳中沉静,不失庄严。 植物的残缺美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残荷因其独特的风姿一直是文人吟诵的对象。深秋褪去繁华的残荷,或倒下或直立,交错复杂,像抽象的几何图。枯黄的败叶,像带着神秘的故事卷缩在一起。秋风吹过,杂乱无章的枝叶摇曳与水相接,素色的枯淡意境,如白色宣纸上行走的墨迹,舒展着优美的舞姿。比起花开的盛世繁华,残荷更有一番萧索的静美。 残缺,在中国艺术的形式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朱良志《艺术之美》中曾写到缺月挂疏桐,意境颇高。又如,中国画中用留白来表现意境,这种留白式的残缺,就像人走入美景,享受似有似无的空灵之美。从相对称的完美,到缺失的美,更像是一种升华,在不失张弛的情况下,给作品注入灵魂,注入故事。 在西方艺术家手中,残缺的陶瓷和碎片,经过层层打磨,从粗到细,粘贴、拼接,构成新的作品,这些饱含历史感的陶器有了新的生命力,如枯草逢春般再次拥有了生息。就如荷兰艺术品修复师布克·戴弗里斯的《时间容器》,残碎的痕迹,用金属粉末镶嵌,就如生命线与呼吸,残缺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母亲的梳妆台上,一直放着一个瓶口破损的花瓶,土灰色的瓶身上,用扭扭歪歪的线条交织成一个“玉”字,虽然不是名贵的艺术品,但却是母亲亲手制作的。只要把花放进花瓶里,花束便会不自觉地向缺口靠拢,不是伸出了头,就是伸出枝叶。这种青春活泼气息,是其他完整花瓶所没有的。它像母亲,年轮在她的脸上留下一道道皱纹,岁月也压弯了她的腰,而她依然由内而外散发着美丽与从容。 残缺亦是美的另一种表达,如黑暗里缓慢升腾的烟火,长久地照亮整个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