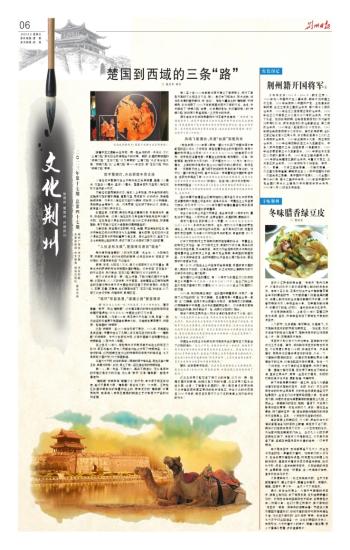|
||||
|
||||
|
□ 张卫平 何川 随着中亚五国峰会召开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汉代“丝绸之路”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同时,战国时期楚国的“玻璃之路”“玉石之路”以及早期的“丝绸之路”也逐渐浮出水面。“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早400年左右,而“玉石之路”则比“玻璃之路”更早。 驼手擎铜灯,开启郢都中西交流 人骑骆驼手擎铜灯出土于荆州地区后港楚墓,器高18.5厘米,灯盘径8.8厘米,盘深1.7厘米。整器由豆形灯盘和人骑骆驼形灯座两部分构成。 双峰骆驼呈昂首前行态;骑驼人上身挺直,两手曲肘前伸托住插有灯柱的管形铜圈,高擎灯盘,昂视前方,似将远行,其造型新颖独特。灯身与人骑骆驼灯座均为铜质,可拆开,系分别铸造,用铅锡合金焊接为一体。灯身素面,骆驼颈下有斜线纹,前腿上部有直线纹用以表示驼毛。 战国至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盛行青铜灯具,形制有鸟形、兽形、扶桑树形等。这种人骑骆驼形灯具在南方楚地考古中为首次发现。骆驼是在沙漠生存的动物,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地,按常理推断,是不可能以骆驼为造型制作青铜器皿的。 文献记载,早在周成王时期,中亚、新疆、蒙古等地的骆驼,就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或作为礼品馈赠。春秋时期,骆驼已作为在沙漠地区军用与民用的重要交通工具。而这盏驼形灯,鉴证了三条千年荆楚丝路的繁茂,讲述了楚文化与西域文明交流的故事。 “人执龙形玉佩”,楚国神玉源自“瑶池” 荆州博物馆馆藏的“人执龙形玉佩”,包含龙、人、太阳等元素,共同构建楚人的对光和热的崇拜;这块玉材质与“和田玉”籽料相似,可猜测其来自“天山瑶池”。 崇拜,祭祀,太阳石人文化,楚文化和西域文化巧然重合,草原流传的萨满教则延续楚国祈福的舞蹈。这件来自“王母瑶池”的天山玉料,则勾勒出“玉石之路”最初的文化交流的形态。 楚文化或许早在一带一路上传播,不断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千百年来,从人文到宗教,方方面面。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玉器与荆州熊家冢发掘出来的玉器文物极度相似,包括玉戈、玉鹰、玉璧、玉璜等,他们侧面印证了“玉石之路”的存在,以及楚文化透过中原,传播西域,影响欧亚。 “琅玕”尽显浪漫,“玻璃之路”爱意情深 一句“随信送上玉佩一枚,问候春君,千万不要两相忘。”情深意重。“琅玕”,别名“蜻蜓眼”,这句情深意浓的诗句出自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精绝国故地)发掘出土的汉文木简。 无独有偶,公元前5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随夫出征的夫差妻子楚国番地暴病夭折。夫差就地厚葬妻子,并随葬一些楚国的“玻璃珠”。 这些“玻璃珠”,在2479年后引起了轰动。1975年,河南固始县侯古堆1号墓中出土了几颗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蜻蜓眼”式玻璃珠。专家分析研究发现,这是我国首次在楚墓中出土玻璃制品,从西方传入楚国。 在上世纪70年代,楚地荆州与中原河南先后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研究人员都在剑格上发现了玻璃饰品。令人惊讶的是,这两把君王宝剑上的玻璃却并非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吴越之国产物,均为楚国制造。 夫差为太子时,抢来的是楚人拥有的西方舶来品;而当夫差为君王后,其佩剑被楚人抢去,装上了楚人自己造出来的玻璃饰品。 同一人,同一物品,不同年代,得到不同结论,无论是西域的尼雅还是东方的夫差,无论是“琅玕”还是“蜻蜓眼”,都是定情信物。 “蜻蜓眼”玻璃珠是“眼睛文化”的产物,其发源于西亚或印度,盛行于草原文明。“蜻蜓眼”是古埃及的一大发明。江陵地区战国中期前后的楚墓中出土的、带有泥芯的“蜻蜓眼”式氟昂斯珠,就是楚人使用已掌握的制造工艺仿制西方产品的实物证据。 楚人至少在2500年前就与西方建立了某种联系,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楚人,通过学习和消化,技术创新,将如此浪漫的器物制作,并“出口”。楚地大量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似乎说明了2000多年前楚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由此,专家提出了“玻璃之路”命题。这浪漫的背后,我们看到楚人的“玻璃之路”的贸易之繁盛和楚人工艺技术的先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先生曾说:“‘蜻蜓眼’玻璃珠虽然小,却是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负载着联结了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的宝贵信息,意义非同寻常。东方的楚国与西方有文化联系,这比汉武帝时张骞的‘凿空’壮举早了约4个世纪。” 凤鸣飞影薄纱,尽显“丝路”荆楚风华 《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有一篇论文谈到了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文中写到:某些巨墓中出土的中国织物,有用大量的橪股细丝线织成(每平方厘米为34×50支)的普通平纹织物。俄罗斯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的,一平方厘米为40×50支纱,宽约43厘米。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对于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曾参与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的彭浩先生,在研究中得出了其“组织结构与我国传统径锦相同,纹样与楚地常见的菱形花纹锦相似”的结论。他在《楚人的纺织与服饰》一书中特别指出:“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刺绣纹样构图与马山一号楚墓的舞龙飞凤纹绣品相同,以花草枝蔓连接着形态各异的凤鸟,左右对称。” 但这件藏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的丝绸绣品残片也与俄罗斯巴泽雷克同为楚国丝织品类似,但是与马山一号墓出土丝织品更为接近;该残片于1976-1978年发掘于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阿拉沟编号为M28的春秋时期墓葬。 综合分析这件丝织品文物特征,结合有关碳14测定资料,墓地延续了相当一个历史阶段,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 测定为春秋阶段的第二十八号墓(碳14测定结论为距今2620±165年),此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二十多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案。由于原件已残破,完整图案形象已难明,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原物现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陈列)。 这件文物的刺绣工艺和荆州博物馆馆藏的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刺绣工艺如出一辙,均为锁绣工艺;其面料为平纹绢,用辫子股绣针法绣出花草、凤鸟等图案。其花纹风格和刺绣技法与荆州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刺绣丝织品,竟然完全相同,是典型的楚国物品。这也间接能佐证,当时楚国的丝织品在丝绸之路沿途,甚至西域均非常受欢迎。 有人认为,这些出土丝织品有可能是楚国、郑国或其它国的商人带到北方去的。这是否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丝绸同域外的交流早于传统的丝绸之路呢? 在发掘该丝织品的墓区,有一个测定为战国至汉代阶段的第三十号墓中(测定数据一为距今2345±75年),出土了除丝织品外包括漆器等文物,该墓地M18、M23、M30出土了战国时代的漆器。 2005年,玛纳斯黑梁湾的一座战国中期墓葬中,发现了一面楚文化风格的四“山”字纹铜镜。巴泽雷克第6号墓出土有一面四“山”纹铜镜,在阿尔泰山西麓也发现过一面相同花纹的铜镜。这种铜镜原产于楚国,流行于战国晚期至秦代。它与具有浓郁楚国风格的织锦、刺绣同出于一地,说明它们的时代相近。 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从物资流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楚地到阿尔泰山北麓,所要经历的困难比楚地到恒河中游大得多。假如当时北方各国出产的丝绸不比楚国出产的逊色,商贩尽可从北方各国采,何苦跑到南方的楚国来,又回头运销到遥远的阿尔泰山北麓去呢?离北方各国近的出口丝绸尚且是楚国的,离北方各国远而离楚国近的出口丝绸就一定也是楚国的了。这虽是推测,但顺理成章。” 中国社会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刘克祥先生依据考古文物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近几十年来,在欧洲和中亚一些地区,相继有早期中国丝绸实物或同丝绸有关的历史文物出土。德国南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中,发现古尸骨骼上沾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公元前5世纪象牙板雕刻的‘阿芙罗狄蒂’,上身穿着透明衣服等,其手法表现均为轻薄的中国丝绸服饰。” 据此,他非常肯定地说,“这些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都说明,最迟公元前5世纪以前,即春秋后期,中国丝绸已经向西传到了欧洲。” 这三条贸易之路见证了楚文化的传播,以及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影响,伴随这些文物的发掘,三条贸易之路也浮出水面,让世人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就已通过贸易将楚文化传播到西域甚至更远的地中海地区,中华文化的光芒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