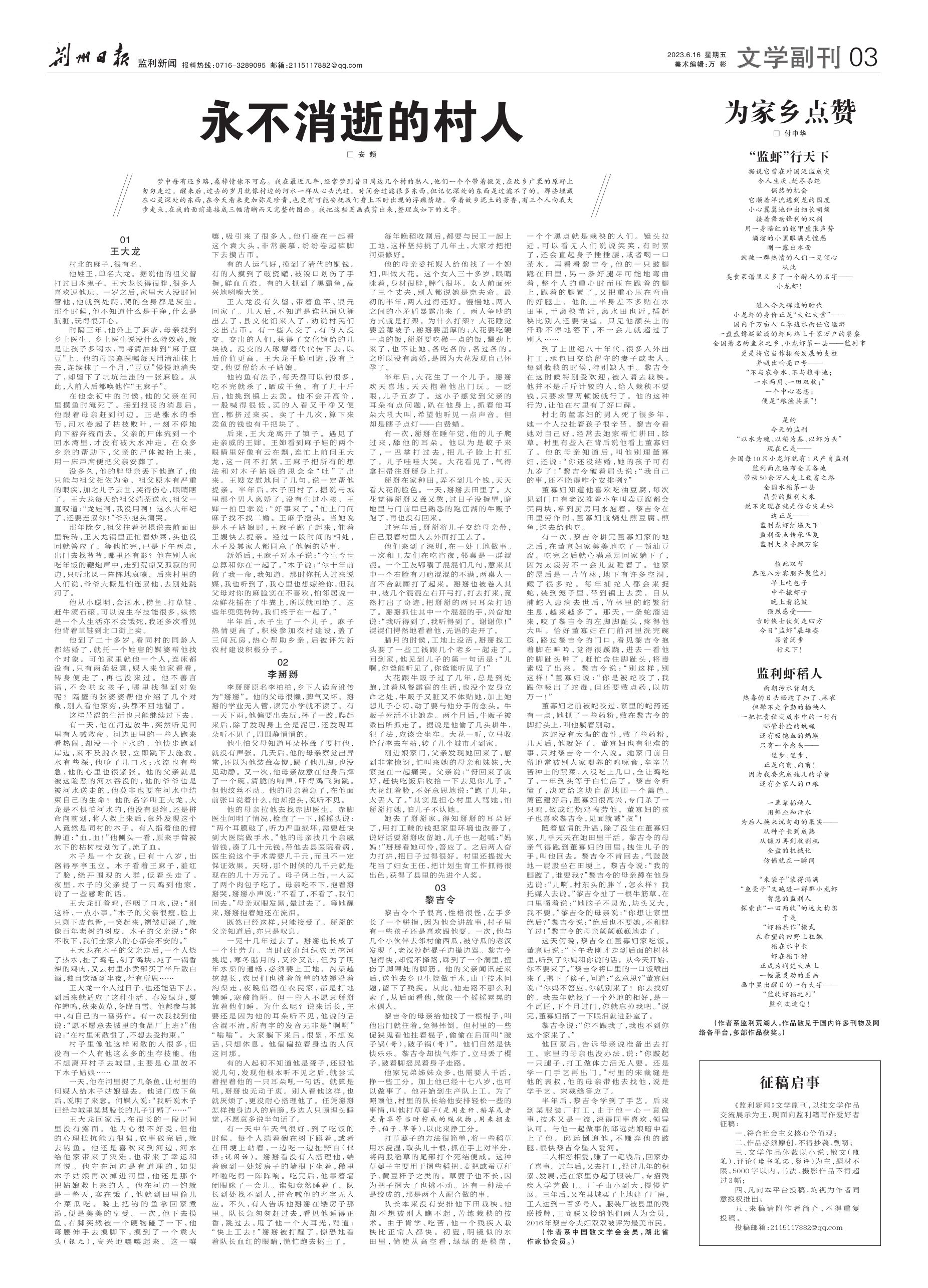|
||||
|
永不消逝的村人 □安频 梦中每有还乡路,桑梓情愫不可忘。我在最近几年,经常梦到昔日周边几个村的熟人,他们一个个带着微笑,在故乡广袤的原野上匆匆走过。醒来后,过去的岁月就像村边的河水一样从心头流过。时间会过滤很多东西,但记忆深处的东西是过滤不了的。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更加弥足珍贵,也更有可能安抚我们身上不时出现的浮躁情绪。带着故乡泥土的芳香,有三个人向我大步走来,在我的面前连接成三幅清晰而又完整的图画。我把这些图画裁剪出来,整理成如下的文字。 村北的麻子,很有名。 他姓王,单名大龙。据说他的祖父曾打过日本鬼子。王大龙长得很胖,很多人喜欢逗他玩。一岁之后,家里大人没时间管他,他就到处爬,爬的全身都是灰尘。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干净,什么是肮脏,玩得很开心。 时隔三年,他染上了麻疹,母亲找到乡土医生。乡土医生说没什么特效药,就是让孩子多喝水,再将清油抹到“麻子豆豆”上。他的母亲遵医嘱每天用清油抹上去,连续抹了一个月,“豆豆”慢慢地消失了,却留下了坑坑洼洼的一张麻脸。从此,人前人后都唤他作“王麻子”。 在他念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河里摸鱼时淹死了。接到报丧的消息后,他跟着母亲赶到河边。正是涨水的季节,河水卷起了枯枝败叶,一刻不停地向下游奔流而去。父亲的尸体流到一个回水湾里,才没有被大水冲走。在众多乡亲的帮助下,父亲的尸体被抬上来,用一床芦席便把父亲安葬了。 没多久,他的胖母亲丢下他跑了,他只能与祖父相依为命。祖父原本有严重的眼疾,加之儿子去世,哭得伤心,眼睛瞎了。王大龙每天给祖父端茶送水,祖父一直叹道:“龙娃啊,我没用啊!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连累你!”爷孙抱头痛哭。 那年除夕,祖父拄着拐棍说去前面田里转转,王大龙锅里正忙着炒菜,头也没回就答应了。等他忙完,已是下午两点,出门去找爷爷,哪里还有影?他在别人家吃年饭的鞭炮声中,走到荒凉又孤寂的河边,只听北风一阵阵地哀嚎。后来村里的人们说,爷爷大概是怕连累他,去别处跳河了。 他从小聪明,会泅水、捞鱼、打草鞋、赶牛滚石磙,可以说生存技能很多,纵然是一个人生活亦不会饿死,我还多次看见他背着草鞋到北口街上卖。 他到了二十多岁,看同村的同龄人都结婚了,就托一个姓唐的媒婆帮他找个对象。可他家里就他一个人,连床都没有,只有两条板凳,媒人来他家看看,转身便走了,再也没来过。他不善言语,不会哄女孩子,哪里找得到对象呢?隔壁的张婆婆帮他介绍了几个对象,别人看他家穷,头都不回地溜了。 这样苦涩的生活也只能继续过下去。有一天,他在河边放牛,突然听见河里有人喊救命。河边田里的一些人跑来看热闹,却没一个下水的。他快步跑到岸边,来不及脱衣服,立即跳下去施救。水有些深,他呛了几口水;水流也有些急,他的心里也很紧张。他的父亲就是被这险恶的河水吞没的,他的爷爷也是被河水送走的,他莫非也要在河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名字叫王大龙,大龙是不惧怕河水的,他没有退缩,还是拼命向前划,将人救上来后,意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同村的木子。有人指着他的臂膊道:“血,血!”他侧头一看,原来手臂被水下的枯树枝划伤了,流了血。 木子是一个女孩,已有十八岁,出落得亭亭玉立。木子看着王麻子,羞红了脸,绕开围观的人群,低着头走了。夜里,木子的父亲提了一只鸡到他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王大龙盯着鸡,吞咽了口水,说:“别这样,一点小事。”木子的父亲很瘦,脸上只剩下皮包骨,一笑起来,褶皱更深了,就像百年老树的树皮。木子的父亲说:“你不收下,我们全家人的心都会不安的。” 王大龙在木子的父亲走后,一个人烧了热水,扯了鸡毛,剁了鸡块,炖了一锅香辣的鸡肉,又去村里小卖部买了半斤散白酒,独自饮酒到半夜,若有所思…… 王大龙一个人过日子,也还能活下去,到后来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春发绿芽,夏作蝉鸣,秋来黄草,冬降白雪。他都参与其中,有自己的一番劳作。有一次我找到他说:“愿不愿意去城里的食品厂上班?”他说:“在村里闲散惯了,不想去受拘束。” 村子里像他这样闲散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有他这么多的生存技能。他不想离开村子去城里,主要是心里放不下木子姑娘…… 一天,他在河里捉了几条鱼,让村里的何媒人给木子姑娘提去。他进门放下鱼后,说明了来意。何媒人说:“我听说木子已经与城里某某股长的儿子订婚了……” 王大龙回家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露面。他内心很不好受,但他的心理抵抗能力很强,农事做完后,就去钓鱼。他还是喜欢来到河边,河水给他家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幸运和喜悦。他守在河边是有道理的,如果木子姑娘再次掉进河里,他还是那个把姑娘救上来的人。他在河边一钓就是一整天,实在饿了,他就到田里偷几个菜瓜吃。晚上把钓的鱼拿回家煮汤,便是美美的享受。一次,他下去摸鱼,右脚突然被一个硬物碰了一下,他弯腰伸手去摸脚下,摸到了一个袁大头(银元),高兴地嚷嚷起来。这一嚷嚷,吸引来了很多人,他们凑在一起看这个袁大头,非常羡慕,纷纷卷起裤脚下去摸古币。 有的人运气好,摸到了清代的铜钱。有的人摸到了破瓷罐,被锐口划伤了手指,鲜血直流。有的人抓到了黑霸鱼,高兴地咧嘴大笑。 王大龙没有久留,带着鱼竿、银元回家了。几天后,不知道是谁把消息捅出去了,县文化馆来人了,劝说村民们交出古币。有一些人交了,有的人没交。交出的人们,获得了文化馆给的几块钱。没交的人琢磨着代代传下去,以后价值更高。王大龙干脆回避,没有上交,他要留给木子姑娘。 他钓鱼有法子,每天都可以钓很多,吃不完就杀了,晒成干鱼。有了几十斤后,他挑到镇上去卖。他不会开高价,一般喊得很低,买的人看又干净又便宜,都挤过来买。卖了十几次,算下来卖鱼的钱也有千把块了。 后来,王大龙离开了镇子。遇见了走亲戚的王婶。王婶看到麻子娃的两个眼睛里好像有云在飘,连忙上前问王大龙,这一问不打紧,王麻子把所有的想法和对木子姑娘的思念全“吐”了出来。王嫂安慰地问了几句,说一定帮他提亲。半年后,木子回村了,据说与城里那个男人离婚了,没有生过小孩。王婶一拍巴掌说:“好事来了。”忙上门问麻子找不找二婚。王麻子摇头。当她说是木子姑娘时,王麻子跳了起来,催着王嫂快去提亲。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木子及其家人都同意了他俩的婚事。 新婚后,王麻子对木子说:“今生今世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木子说:“你十年前救了我一命,我知道。那时你托人过来说媒,我也听到了,我心里也想嫁给你,但我父母对你的麻脸实在不喜欢,怕邻居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所以就回绝了。这些年兜兜转转,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半年后,木子生了一个儿子。麻子热情更高了,积极参加农村建设,盖了三间瓦房,热心帮助乡亲,后被评为新农村建设积极分子。 02李掰掰 李掰掰原名李柏柏,乡下人读音讹传为“掰掰”。他的父母很懒,脾气又坏。掰掰的学业无人管,读完小学就不读了。有一天下雨,他偏要出去玩,摔了一跤,爬起来后,除了发现身上全是泥巴,还发现耳朵听不见了,周围静悄悄的。 他生怕父母知道耳朵摔聋了要打他,就没有声张。几天后,他的母亲察觉出异常,还以为他装聋卖傻,踢了他几脚,也没见动静。又一次,他母亲故意在他身后摔了一个碗,清脆的响声,吓得鸡飞狗跳。但他纹丝不动。他的母亲着急了,在他面前张口说着什么,他却摇头,说听不见。 他的母亲拉他去找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问明了情况,检查了一下,摇摇头说:“两个耳膜破了,听力严重损坏,需要赶快到大医院做手术。”他的母亲找几个亲戚借钱,凑了几十元钱,带他去县医院看病,医生说这个手术需要几千元,而且不一定保证效果。天呀,那个时候的几千元就是现在的几十万元了。母子俩上街,一人买了两个肉包子吃了。母亲吃不下,抱着掰掰哭,掰掰小声说:“不看了,不看了,我们回去。”母亲双眼发黑,晕过去了。等她醒来,掰掰抱着她还在流泪。 既然已经这样,只能接受了。掰掰的父亲知道后,亦只是叹息。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掰掰也长成了一个壮劳力。当时政府组织农民挖河挑堤,寒冬腊月的,又冷又冻,但为了明年水渠的通畅,必须要上工地。沟渠越挖越长,农民们也挑着简单的被褥沿着沟渠走,夜晚借宿在农民家,都是打地铺睡,寒酸简陋。但一些人不愿意掰掰靠着他们睡。为什么呢?说来话长,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耳朵听不见,他说的话含混不清,所有字的发音无非是“啊啊”“嗡嗡”。大家躺下来后,很累,不想说话,只想休息。他偏偏拉着身边的人问这问那。 有的人起初不知道他是聋子,还跟他说几句,发现他根本听不见之后,就尝试着捏着他的一只耳朵吼一句话。就算是吼,掰掰也无动于衷。别人看他这样,也就厌烦了,更没耐心搭理他了。任凭掰掰怎样拽身边人的肩膀,身边人只顾埋头睡觉,不愿意多说半句话了。 有一天中午天气很好,到了吃饭的时候。每个人端着碗在树下蹲着,或者在田埂上站着,一边吃一边扯野白(俚语:说闲话)。掰掰看没有人搭理他,端着碗到一处矮房子的墙根下坐着,稀里哗啦吃得一阵阵响。吃完后,他靠着墙闭眼眯了一会儿。谁知竟然睡着了。队长到处找不到人,拼命喊他的名字无人应。不久,有人告诉他掰掰在矮房子那里。队长急匆匆赶过去,看见他睡得正香,跳过去,甩了他一个大耳光,骂道:“快上工去!”掰掰被打醒了,惊恐地看着队长血红的眼睛,慌忙跑去挑土了。 每年晚稻收割后,都要与民工一起上工地,这样坚持挑了几年土,大家才把把河渠修好。 他的母亲委托媒人给他找了一个媳妇,叫做大花。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眼睛眯着,身材很胖,脾气很坏。女人前面死了三个丈夫,别人都说她是克夫命。最初的半年,两人过得还好。慢慢地,两人之间的小矛盾暴露出来了。两人争吵的方式就是打架。为什么打架?大花睡觉要盖薄被子,掰掰要盖厚的;大花要吃硬一点的饭,掰掰要吃稀一点的饭,犟劲上来了,也不让她,各吃各的,各过各的。之所以没有离婚,是因为大花发现自己怀孕了。 半年后,大花生了一个儿子。掰掰欢天喜地,天天抱着他出门玩。一眨眼,儿子五岁了。这小子感觉到父亲的耳朵有点问题,趴在他身上,抓着他耳朵大吼大叫,希望他听见一点声音。但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有一次,掰掰在睡午觉,他的儿子爬过来,舔他的耳朵。他以为是蚊子来了,一巴掌打过去,把儿子脸上打红了。儿子哇哇大哭。大花看见了,气得拿扫帚往掰掰身上打。 掰掰在家种田,弄不到几个钱,天天看大花的脸色。一天,掰掰去田里了。大花觉得掰掰又聋又憨,过日子没指望,暗地里与门前早已熟悉的跑江湖的牛贩子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过完年后,掰掰将儿子交给母亲带,自己跟着村里人去外面打工去了。 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一处工地做事。一次和工友们在吃宵夜,邻桌是一群混混。一个工友嘟囔了混混们几句,惹来其中一个右脸有刀疤混混的不满,两桌人一言不合就厮打了起来。掰掰也被卷入其中,被几个混混左右开弓打,打去打来,竟然打出了奇迹,把掰掰的两只耳朵打通了。掰掰抓住其中一个混混的手,兴奋地说:“我听得到了,我听得到了。谢谢你!”混混们愕然地看着他,无语的走开了。 腊月的时候,工地上没活,掰掰找工头要了一些工钱跟几个老乡一起走了。回到家,他见到儿子的第一句话是:“儿啊,你爸能听见了,你爸能听见了!” 大花跟牛贩子过了几年,总是到处跑,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也没个安身立命之处,牛贩子又脏又不体贴她,加上她想儿子心切,动了要与他分手的念头。牛贩子死活不让她走。两个月后,牛贩子被派出所抓走了。据说是他偷了几头耕牛,犯了法,应该会坐牢。大花一听,立马收拾行李去车站,转了几个城市才到家。 刚进娘家门,父亲发现她回来了,感到非常惊讶,忙叫来她的母亲和妹妹,大家抱在一起痛哭。父亲说:“伢回来了就好,赶快吃饭后收拾一下去见你儿子。”大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跑了几年,太丢人了。”其实是担心村里人骂她,怕掰掰打她,怕儿子不认她。 她去了掰掰家,得知掰掰的耳朵好了,用打工赚的钱把家里环境也改善了,说好话要掰掰收留她,儿子也一起喊:“妈妈!”掰掰看她可怜,答应了。之后两人奋力打拼,把日子过得很好。村里还提拔大花当了妇女主任,把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出色,获得了县里的先进个人奖。 03黎吉令 黎吉令个子很高,性格很怪,左手多长了一个骈指,因为他会讲故事,村子里有一些孩子还是喜欢跟他耍。一次,他与几个小伙伴去邻村偷西瓜,被守瓜的老汉发现了,老汉抄起棍子边撵边骂。黎吉令跑得快,却慌不择路,踩到了一个洞里,扭伤了脚踝处的脚筋。他的父亲闻讯赶来后,送他去乡卫生院做手术,由于技术问题,留下了残疾。从此,他走路不那么利索了,从后面看他,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偶人。 黎吉令的母亲给他找了一根棍子,叫他出门就拄着,免得摔倒。但村里的一些促狭鬼看他拄着棍子,偷偷在后面叫“跛子锅(哥),跛子锅(哥)”。他们自然是快快乐乐。黎吉令却快气炸了,立马丢了棍子,跛着脚摇晃着身子走路。 他家兄弟姊妹众多,也需要人干活,挣一些工分。加上他已经十七八岁,也可以做事了。他开始到生产队上工。为了照顾他,村里的队长给他安排轻松一些的事情,叫他打草葽子(是用麦秆、稻草或者是青草等临时拧成的绳状物,用来捆麦子、稻子、草等),以此来挣工分。 打草葽子的方法很简单,将一些稻草用水浸湿,取头儿十根,抓在手上对半分,将两股稻草的尾部打个死结便成。这种草葽子主要用于捆些稻把、麦把或蚕豆秆子、黄豆秆子之类的。草葽子也不长,因为把子捆大了也挑不动。还有一种法子是绞成的,那是两个人配合做的事。 队长本来没有安排他下田栽秧,他却不想被别人瞧不起,苦练栽秧的技术。由于肯学、吃苦,他一个残疾人栽秧比正常人都快。初夏,明镜似的水田里,倘使从高空看,绿绿的是秧苗, 一个个黑点就是栽秧的人们。镜头拉近,可以看见人们说说笑笑,有时累了,还会直起身子捶捶腰,或者喝一口茶水。再看看黎吉令,他的一只跛腿跪在田里,另一条好腿尽可能地弯曲着,整个人的重心时而压在跪着的腿上,跪着的腿累了,又把重心压在弯曲的好腿上。他的上半身差不多贴在水田里,手离秧苗近,离水田也近,插起秧比别人还要快些。只见他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落下,不一会儿就超过了别人……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人外出打工,承包田交给留守的妻子或老人。每到栽秧的时候,特别缺人手。黎吉令在这时候特别受欢迎,被人请去栽秧。他并不是斤斤计较的人,给人栽秧不要钱,只要求管两顿饭就行了。他的这种行为,让他在村里有了好口碑。 村北的董寡妇的男人死了很多年,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很辛苦。黎吉令看她对自己好,经常去她家帮忙耕田、除草。村里有些人在背后说他看上董寡妇了。他的母亲知道后,叫他别理董寡妇,还说:“你还没结婚,她的孩子可有九岁了!”黎吉令皱着眉头说:“我自己的事,还不晓得咋个安排咧?” 董寡妇知道他喜欢吃油豆腐,每次见到门口有老汉推着小车叫卖豆腐都会买两块,拿到厨房用水泡着。黎吉令在田里劳作时,董寡妇就烧灶煎豆腐、煎鱼,送去给他吃。 有一次,黎吉令耕完董寡妇家的地之后,在董寡妇家美美地吃了一顿油豆腐。吃完之后就心满意足回家躺下了,因为太疲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家的屋后是一片竹林,地下有许多空洞,藏了很多蛇。每年捕蛇人都会来捉蛇,装到笼子里,带到镇上去卖。自从捕蛇人患病去世后,竹林里的蛇繁衍生息,越来越多了。那天,一条蛇溜进来,咬了黎吉令的左脚脚趾头,疼得他大叫。恰好董寡妇在门前河里洗完碗筷,路过黎吉令的门口,看见黎吉令抱着脚在呻吟,觉得很蹊跷,进去一看他的脚趾头肿了,赶忙含住脚趾头,将毒素吸了出来。黎吉令说:“别这样,别这样!”董寡妇说:“你是被蛇咬了,我跟你吸出了蛇毒,但还要敷点药,以防万一!” 董寡妇之前被蛇咬过,家里的蛇药还有一点,她抓了一些药粉,敷在黎吉令的脚指头上,叫他躺着别动。 这蛇没有太强的毒性,敷了些药粉,几天后,他就好了。董寡妇也有犯难的事,只对黎吉令一个人说。她家门前自留地常被别人家喂养的鸡啄食,辛辛苦苦种上的蔬菜,人没吃上几口,全让鸡吃了,一年到头等于白忙活了。黎吉令听懂了,决定给这块自留地围一个篱笆。篱笆建好后,董寡妇很高兴,专门杀了一只鸡,做成红烧鸡犒劳他。董寡妇的孩子也喜欢黎吉令,见面就喊“叔”! 随着感情的升温,除了没住在董寡妇家,几乎天天在她田里干活。黎吉令的母亲气得跑到董寡妇的田里,拽住儿子的手,叫他回去。黎吉令不肯回去,气鼓鼓地一屁股坐在田埂上。黎吉令说:“我的腿跛了,谁要我?”黎吉令的母亲蹲在他身边说:“儿啊,村东头的胖丫,怎么样?我托媒人去说。”黎吉令扯了一根牛筋草,在口里嚼着说:“她脑子不灵光,块头又大,我不要。”黎吉令的母亲说:“你想让家里绝后?”黎吉令说:“绝后也不要她,不和胖丫过!”黎吉令的母亲颤颤巍巍地走了。 这天傍晚,黎吉令在董寡妇家吃饭。董寡妇说:“下午我刚才走到后面的树林里,听到了你妈和你说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来了。”黎吉令将口里的一口饭喷出来了,撂下了筷子,问道:“么意思?”董寡妇说:“你妈不答应,你就别来了!你去找好的。我去年就找了一个外地的相好,是一个瓦匠,下个月过门,你就忘掉我吧。”说完,董寡妇揩了一下眼泪就进卧室了。 黎吉令说:“你不跟我了,我也不到你这个家来了。” 他回家后,告诉母亲说准备出去打工。家里的母亲也没办法,说:“你跛起一只腿子,打工做体力活无人要。还是学一门手艺再出门。”村里的宋裁缝是他的表叔,他的母亲带他去找他,说是学手艺。宋裁缝答应了。 半年后,黎吉令学到了手艺。后来到某服装厂打工,由于他一心一意做事,技术又是一流,深得同事喜欢、领导认可。与他一起做事的邱远姑娘暗中看上了他。邱远倒追他,不嫌弃他的跛腿,很快黎吉令坠入爱河。 二人相恋相爱,赚了一笔钱后,回家办了喜事。过年后,又去打工,经过几年的积累、发展,还在家里办起了服装厂,专招残疾人学艺做工。厂子由小到大,慢慢扩展。三年后,又在县城买了土地建了厂房,工人达到一百多号人。服装厂被县里的残联授牌,工商联又接纳他们两人为会员,2016年黎吉令夫妇双双被评为最美市民。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