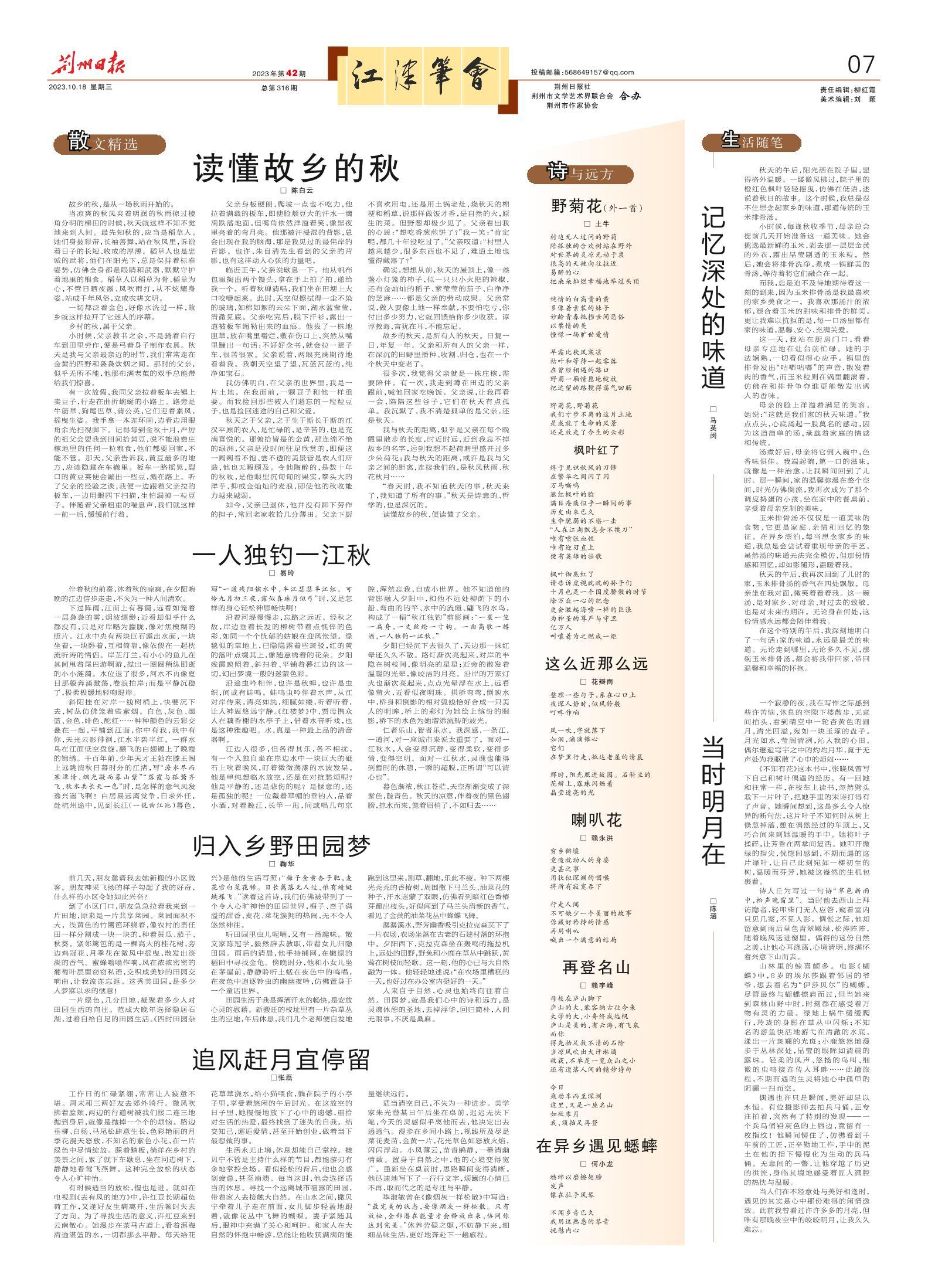□ 陈白云
故乡的秋,是从一场秋雨开始的。
当凉爽的秋风夹着明润的秋雨掠过棱角分明的梯田的时候,秋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到人间。最先知秋的,应当是稻草人。她们身披彩带,长袖善舞,站在秋风里,诉说着日子的长短、收成的厚薄。稻草人也是忠诚的武将,他们在阳光下,总是保持着标准姿势,仿佛全身都是眼睛和武器,默默守护着地里的粮食。稻草人以稻草为骨、稻草为心,不管日晒夜露、风吹雨打,从不炫耀身姿,站成千年风俗,立成农耕文明。
一切都泛着金色,好像水洗过一样,故乡就这样拉开了它迷人的序幕。
乡村的秋,属于父亲。
小时候,父亲教书之余,不是骑着自行车到田里劳作,便是弓着身子制作农具。秋天是我与父亲最亲近的时节,我们常常走在金黄的四野和袅袅炊烟之间。那时的父亲,似乎无所不能,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总能带给我们惊喜。
有一次放假,我同父亲拉着板车去镇上卖豆子,行走在曲折蜿蜒的小路上。路旁是牛筋草、狗尾巴草、蒲公英,它们迎着素风,摇曳生姿。我手拿一本连环画,边看边用眼角余光扫视脚下。记得每到金秋十月,严厉的祖父会要我到田间拾黄豆,说不能浪费庄稼地里的任何一粒粮食,他们都要回家,不能不管。那天,父亲告诉我,黄豆最多的地方,应该隐藏在车辙里。板车一路摇晃,裂口的黄豆荚便会蹦出一些豆,溅在路上。听了父亲的经验之谈,我便一边跟着父亲拉的板车,一边用眼四下扫描,生怕漏掉一粒豆子。伴随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缓缓前行着。
父亲身板硬朗,爬坡一点也不吃力,他拉着满载的板车,即使脸颊豆大的汗水一滴滴跌落地面,但嘴角依然洋溢着笑,像黑夜里亮着的弯月亮。他那被汗浸湿的背影,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见过的最伟岸的背影。也许,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父亲的背影,也有这样动人心弦的力量吧。
临近正午,父亲说歇息一下。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拿在手上拍了拍,递给我一个。听着秋蝉清唱,我们坐在田埂上大口咬嚼起来。此时,天空似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玻璃,如棉如絮的云朵下面,湖水蓝莹莹,清澈见底。父亲吃完后,脱下汗衫,露出一道被板车绳勒出来的血痕。他拔了一株地胆草,放在嘴里嚼烂,敷在伤口上,突然从嘴里蹦出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就会拉一辈子车,很苦很累。父亲说着,两眼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朝天空望了望,瓦蓝瓦蓝的,纯净如宝石。
我仿佛明白,在父亲的世界里,我是一片土地。在我面前,一颗豆子和他一样重要。而我捡回那些被人们遗忘的一粒粒豆子,也是捡回迷途的自己和父爱。
秋天之于父亲,之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汉平原的农人,是忙碌的,是辛苦的,也是充满喜悦的。那俯拾皆是的金黄,那连绵不绝的绿洲,父亲是没时间驻足欣赏的,即便这一阙阙看不饱、尝不透的美景皆是农人们所造,他也无暇顾及。令他陶醉的,是数十年的秋收,是他眼里沉甸甸的果实,拳头大的洋芋,抑或金灿灿的麦浪,即使他的秋收能力越来越弱。
如今,父亲已退休,他并没有卸下劳作的担子,常回老家收拾几分薄田。父亲下厨不喜欢用电,还是用土锅老灶,烧秋天的棉梗和稻草,说那样做饭才香,是自然的火,原生的菜。但野葱却极少见了。父亲看出我的心思:“想吃香葱煎饼了?”我一笑:“肯定呢,都几十年没吃过了。”父亲叹道:“村里人越来越少,很多东西也不见了,难道土地也懂得藏器了?”
确实,想想从前,秋天的屋顶上,像一盏盏小灯笼的柿子,似一只只小火把的辣椒,还有金灿灿的稻子、紫莹莹的茄子、白净净的芝麻……都是父亲的劳动成果。父亲常说,做人要像土地一样奉献,不要怕吃亏,你付出多少努力,它就回馈给你多少收获。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不能忘记。
故乡的秋天,是所有人的秋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和所有人的父亲一样,在深沉的田野里播种、收割、归仓,也在一个个秋天中变老了。
很多次,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株庄稼,需要陪伴。有一次,我走到蹲在田边的父亲跟前,喊他回家吃晚饭。父亲说,让我再看一会,陪陪这些谷子,它们在秋天有点孤单。我沉默了,我不清楚孤单的是父亲,还是秋天。
我与秋天的距离,似乎是父亲在每个晚霞里散步的长度,时近时远,近到我忘不掉故乡的名字,远到我想不起荷塘里盛开过多少朵荷花;我与秋天的距离,或许是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连接我们的,是秋风秋雨、秋花秋月……
“春天时,我不知道秋天的事,秋天来了,我知道了所有的事。”秋天是诗意的、哲学的,也是深沉的。
读懂故乡的秋,便读懂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