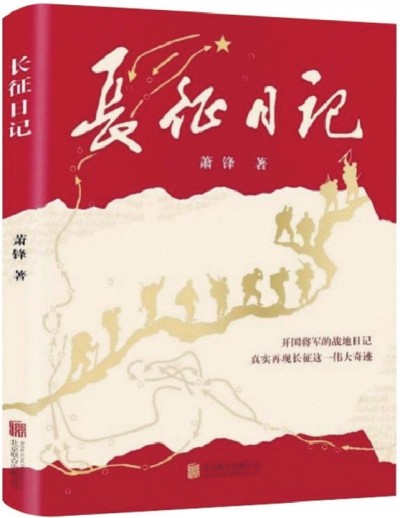□ 陈宇
萧锋的《长征日记》最早出版于1979年,一经问世便风靡全国,迄今已出版了多个版本。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在大学的军事历史课上,听老师专题讲解过这本书。萧锋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艰苦岁月里,依然不间断地写下十多万字的长征日记。他的精神让我这个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军人,甚为钦佩,备受鼓舞。
萧锋出身贫苦,参军前是个放牛郎,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他学习识字、造句、作文都是在参加红军之后。战友告诉他,可以把火热的战斗生活记录下来,这样不仅可以巩固识字学文化的成果,还可以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于是他边学习识字,边用土草纸和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写日记。这个习惯,他坚持了60多年。
参加长征的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部队,近20万人,但写日记的仅十余人,他们的日记现已成为极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萧锋是十余人中坚持写日记时间最长的人,其日记也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一本。通过这本日记,我们不仅能看到作者的思想高度,还能看到红军英勇顽强、坚信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有句震撼全军的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在红军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战士的文化教育,把“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并列为三大教育。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组织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以提高基层指挥员的军事素养和文化素养。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对军队文化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坚持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
长征出发的当月,萧锋在日记中写道:“行军途中遇见谭政主任……他还说,‘连队要积极开展行军识字运动,一人一天认一个字,一年就可认三百六十多个字。扫除文盲,才能更好地学习革命的理论。’”
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紧张时期,周恩来副主席对萧锋说:“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搞好宣传工作,使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播下革命的火种。”周恩来又指着战士背着的“站好岗”识字牌称赞说:“既打仗行军,又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我们工农现在打仗需要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
“四渡赤水”名扬红军长征史,萧锋所在的红一师则是“八渡赤水”。在紧张的行军作战期间,红一师仍要求:“各部队要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能写字的人,用木炭、毛笔,用大字、小字,在墙壁和门板上写上瓦解白军的标语。从连队到军团的军政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自己动手,把瓦解白军的标语写满整个宿营地”。
苟坝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巩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又一重要会议。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定出奇兵,由东向西三渡赤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萧锋所在的部队依然坚持文化学习,他在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行军识字做得好,七连班长刘新文一天行军识字12个,就是那个‘打圈子’的‘圈’。字难写,我看先易后难总可学会。”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萧锋写道:“凌晨五时由罗家沟出发,到贺家坪宿营,行程70里。团部对行军识字工作抓得很紧,战士们用硬纸和树皮做成牌子,写上字,边行军,边认字,效果很好。”
萧锋就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学习氛围中,伴着炮火和硝烟,写下了长征日记。
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萧锋有了相对稳定的休息时间,他将污渍斑斑、字迹模糊的原始日记誊抄在笔记本上。此后又在养伤期间,找有关领导和战友核实,对日记进行补充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走长征路,对日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一一核对和修订,最终形成了这部《长征日记》,其字里行间闪耀着红军指战员奋斗(红军不怕远征难)、乐观(万水千山只等闲)、进取(而今迈步从头越)、坚韧(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辉煌的精神谱系,长征精神就是其中之一。“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长征是红军历史上一次满怀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萧锋在炮火硝烟中写下的日记,则是精神层面上的远征。学习长征精神,萧锋的《长征日记》不可不读;研究长征历史,《长征日记》更应是案头常备的工具书;重走长征路,《长征日记》不仅是长征路上的道路地标,也是遇到困难挫折时不屈不挠的精神坐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人活着,本身就是一次长征,途中需给思想“补钙”,为精神“加油”。读一遍《长征日记》,仿佛重走了一遍艰辛的长征路,让我们能更深刻地感悟长征精神,明白长征精神是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自觉地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长征日记》再版之际,我受萧锋之女萧南溪大姐嘱托,写下以上文字,权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