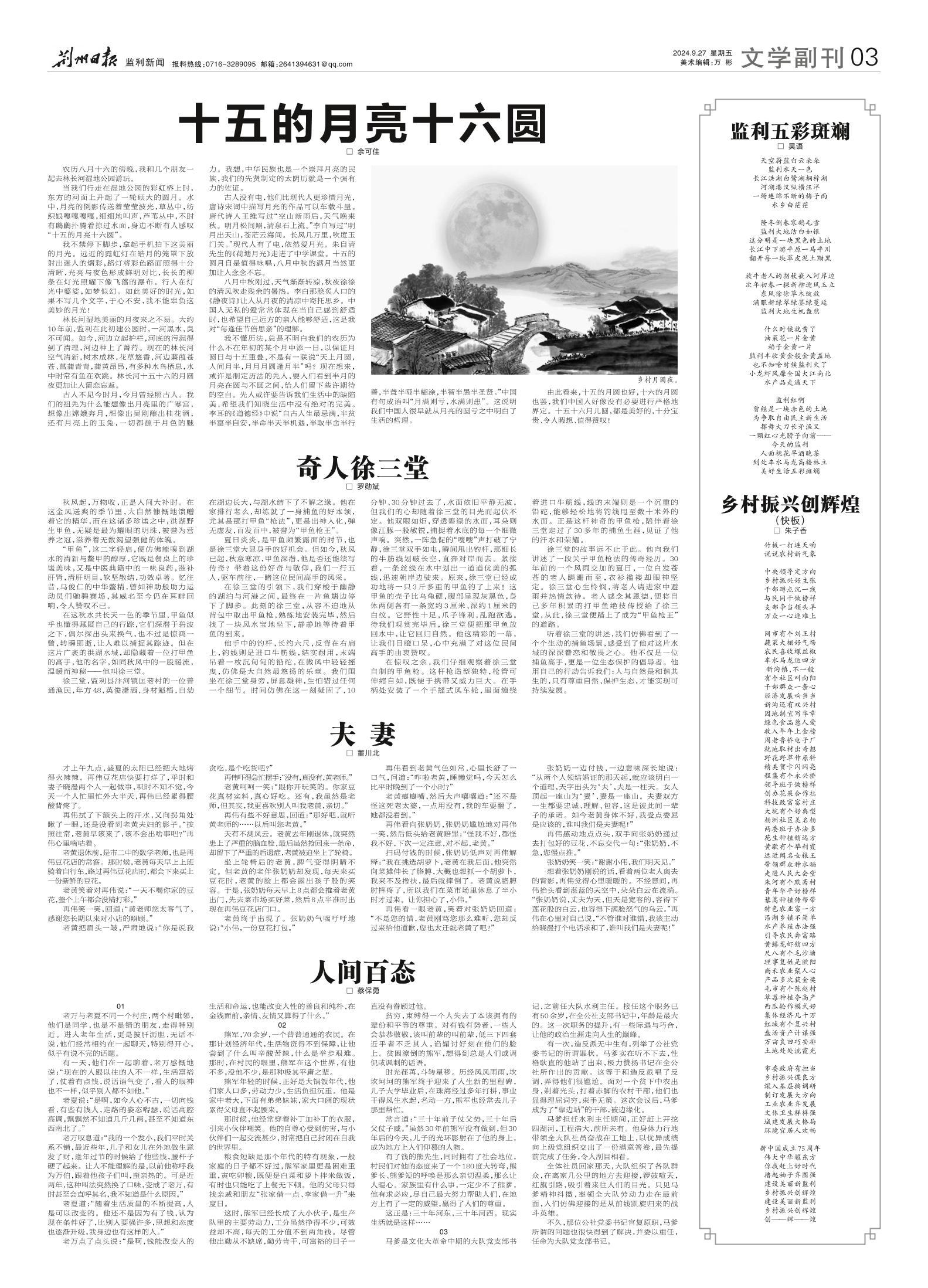□ 蔡保勇
01
老万与老夏不同一个村庄,两个村毗邻,他们是同学,也是不是错的朋友,走得特别近。进入老年生活,更是披肝沥胆,无话不说,他们经常相约在一起聊天,特别得开心,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聊着,老万感慨地说:“现在的人跟以往的人不一样,生活富裕了,仗着有点钱,说话语气变了,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似乎别人都不如他。”
老夏说:“是啊,如今人心不古,一切向钱看,有些有钱人,走路的姿态嘚瑟,说话高腔高调,飘飘然不知道几斤几两,甚至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老万叹息道:“我的一个发小,我们平时关系不错,最近些年,儿子和女儿在外地做生意发了财,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了他些钱,腰杆子硬了起来。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以前他称呼我为万伯,跟着他孩子们叫,蛮亲热的。可是近两年,这种叫法突然换了口味,变成了老万,有时甚至会直呼其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老夏道:“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是可以改变的。他还不是因为有了钱,认为现在条件好了,比别人要强许多,思想和态度也逐渐升级,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老万点了点头说:“是啊,钱能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也能改变人性的善良和纯朴,在金钱面前,亲情、友情又算得了什么。”02
熊军,70余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让他尝到了什么叫辛酸苦辣,什么是举步艰难。那时,在村民的眼里,熊军在这个世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是那种极其平庸之辈。
熊军年轻的时候,正好是大锅饭年代,他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负担沉重。他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弟弟妹妹,家大口阔的现状累得父母直不起腰来。
那时候,他经常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引来小伙伴嘲笑。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与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甚少,时常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
粮食短缺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现象,一般家庭的日子都不好过,熊军家里更是困难重重,寅吃卯粮,既便是白菜和萝卜拌米做饭,有时也只能吃了上餐无下顿。他的父母只得找亲戚和朋友“张家借一点、李家借一升”来度日。
这时,熊军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工分虽然挣得不少,可效益却不高,每天的工分值不到两角钱。尽管他出勤从不缺席,勤劳肯干,可富裕的日子一直没有眷顾过他。
贫穷,束缚得一个人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辈份和平等的尊重。对有钱有势者,一些人会恭恭敬敬,该叫前辈的叫前辈,低三下四套近乎者不乏其人,谄媚讨好刻在他们的脸上。贫困潦倒的熊军,想得到总是人们或调侃或讽刺的话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熊军终于迎来了人生新的里程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珠海经过多年打拼,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名动一方,熊军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忙。
常言道:“三十年前子仗父势,三十年后父仗子威。”虽然30年前熊军没有做到,但30年后的今天,儿子的光环影射在了他的身上,成为地方上人们仰慕的人物。
有了钱的熊先生,同时拥有了社会地位,村民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熊爹长、熊爹短的呼唤是那么亲切温柔,那么让人暖心。家族里有什么事,一定少不了熊爹,他有求必应,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人们,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威望,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这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03马爹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的大队党支部书
记,之前任大队水利主任。接任这个职务已有50余岁,在全公社支部书记中,年龄是最大的。这一次职务的提升,有一些际遇与巧合,让他的政治生涯走向人生的巅峰。
有一次,造反派无中生有,列举了公社党委书记的所谓罪状。马爹实在听不下去,性格耿直的他站了出来,极力赞扬书记在全公社所作出的贡献。这等于和造反派唱了反调,弄得他们很尴尬。面对一个贫下中农出身,剃着光头,打着赤脚的农村干部,他们也显得理屈词穷,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后,马爹成为了“靠边站”的干部,被边缘化。
马爹担任水利主任期间,正好赶上开挖四湖河,工程浩大,前所未有。他身体力行地带领全大队社员奋战在工地上,以优异成绩向上级党组织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最先提前完成了任务,令人刮目相看。
全体社员回家那天,大队组织了各队群众,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去迎接,锣鼓喧天,红旗引路,吸引着来往人们的目光。只见马爹精神抖擞,率领全大队劳动力走在最前面,人们仿佛迎接的是从前线凯旋归来的战斗英雄。
不久,那位公社党委书记官复原职,马爹所谓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并委以重任,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