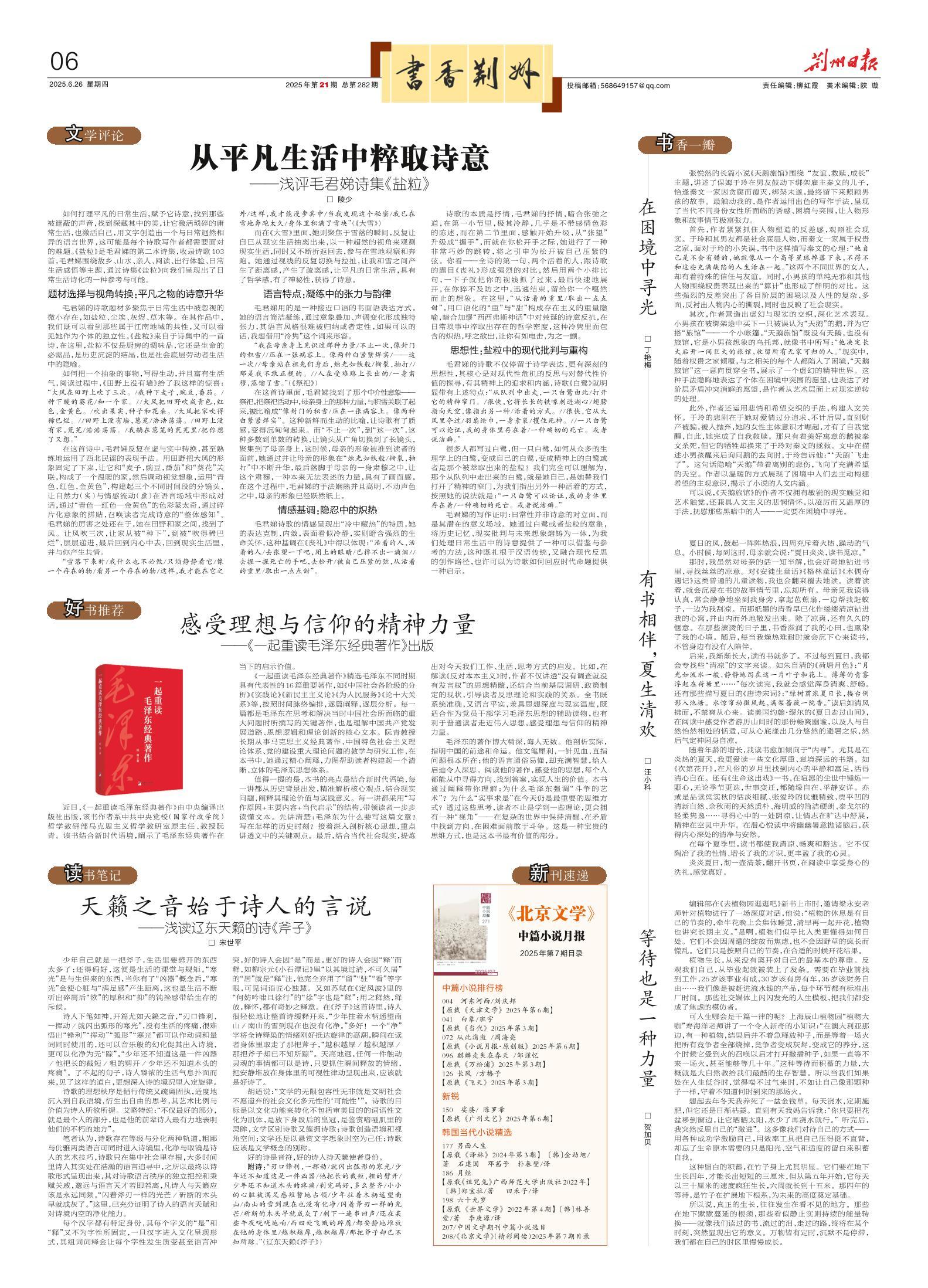□ 陵少
如何打理平凡的日常生活,赋予它诗意,找到那些被遮蔽的声音,找到深藏其中的美,让它激活琐碎的庸常生活,也激活自己,用文字创造出一个与日常迥然相异的语言世界,这可能是每个诗歌写作者都需要面对的难题。《盐粒》是毛君娣的第二本诗集,收录诗歌103首,毛君娣围绕故乡、山水、亲人、阅读、出行体验、日常生活感悟等主题,通过诗集《盐粒》向我们呈现出了日常生活诗化的一种参考与可能。
题材选择与视角转换:平凡之物的诗意升华
毛君娣的诗歌题材多聚焦于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微小存在,如盐粒、尘埃、灰烬、草木等。在其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那些属于江南地域的共性,又可以看见她作为个体的独立性。《盐粒》来自于诗集中的一首诗,在这里,盐粒不仅是厨房的调味品,它还是生命的必需品,是历史沉淀的结晶,也是社会底层劳动者生活中的隐喻。
如何把一个抽象的事物,写得生动,并且富有生活气,阅读过程中,《田野上没有墙》给了我这样的惊喜:“大风在田野上吹了三次。/我种下麦子,豌豆,番茄。/种下暖的葵花/和一个家。//大风把田野吹成青色,红色,金黄色。/吹出果实,种子和花朵。/大风把家吹得稀巴烂。//田野上没有墙,葱茏/浩浩荡荡。/田野上没有家,荒芜/浩浩荡荡。/我躺在葱茏的荒芜里/把你想了又想。”
在这首诗中,毛君娣反复在虚与实中转换,甚至熟练地运用了西北民谣的表现手法。用田野把大风的形象固定了下来,让它和“麦子,豌豆,番茄”和“葵花”关联,构成了一个温暖的家,然后调动视觉想象,运用“青色,红色,金黄色”,构建起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分镜头,让自然力(实)与情感流动(虚)在语言场域中形成对话,通过“青色—红色—金黄色”的色彩蒙太奇,通过碎片化意象的拼贴,召唤读者完成诗意的“整体感知”。毛君娣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她在田野和家之间,找到了风。让风吹三次,让家从被“种下”,到被“吹得稀巴烂”,层层递进,最后回到内心中去,回到现实生活里,并与你产生共情。
“雪落下来时/我什么也不必做/只须静静看它/像一个存在的物/看另一个存在的物/这样,我才能在它之外/这样,我才能漫步其中/当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已在雪地奔跑太久/身体里积满了雪块”(《大雪》)
而在《大雪》里面,她则聚焦于雪落的瞬间,反复让自已从现实生活抽离出来,以一种超然的视角来观测现实生活,同时又不断折返回去,参与在雪地观察和奔跑。她通过视线的反复切换与拉扯,让我和雪之间产生了距离感,产生了疏离感,让平凡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哲学感,有了神秘性,获得了诗意。
语言特点:凝练中的张力与韵律
毛君娣用的是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表达方式,她的语言简洁凝练,通过意象叠加、声调变化形成独特张力,其语言风格很难被归纳或者定性,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用“冷隽”这个词来形容。
“我在母亲身上见识过那种力量/不止一次,像封门的积雪//压在一张病容上。像两种白紧紧焊实/——这一次//母亲站在祖先们身后,烛光如铁般/撕裂,抽打//那是我不敢正视的。//人在受难路上长出的/一身肃穆,蒸馏了雪。”(《祭祀》)
在这首诗里面,毛君娣找到了那个中介性意象——祭祀,把祭祀活动中,母亲身上的那种力量,与积雪关联了起来,被比喻成“像封门的积雪/压在一张病容上。像两种白紧紧焊实”。这种新鲜而生动的比喻,让诗歌有了质感,变得沉甸甸起来。而“不止一次”,到“这一次”,这种多数到单数的转换,让镜头从广角切换到了长镜头,聚集到了母亲身上,这时候,母亲的形象被推到读者的面前,她通过并让母亲的形象在“烛光如铁般/撕裂,抽打”中不断升华,最后落脚于母亲的一身肃穆之中,让这个肃穆,一种本来无法表述的力量,具有了画面感,在这个过程中,毛君娣的手法娴熟并且高明,不动声色之中,母亲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情感基调:隐忍中的炽热
毛君娣诗歌的情感呈现出“冷中藏热”的特质,她的表达克制、内敛,表面看似冷静,实则暗含强烈的生命关怀,这种基调在《丧礼》中得以体现:“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去张望一下吧,闭上的眼睛/已掉不出一滴泪//去握一握死亡的手吧,去松开/被自己压紧的弦,从活着的重里/取出一点点甜”。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毛君娣的抒情,暗合张弛之道,在第一小节里,极其冷静,几乎是不带感情色彩的陈述,而在第二节里面,感触开始升级,从“张望”升级成“握手”,而就在你松开手之际,她进行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跳转,将之引申为松开被自己压紧的弦。你看——全诗的第一句,两个活着的人,跟诗歌的题目《丧礼》形成强烈的对比,然后用两个小排比句,一下子就把你的视线抓了过来,最后快速地展开,在你猝不及防之中,迅速结束,留给你一个嘎然而止的想象。在这里,“从活着的重里/取出一点点甜”,用口语化的“重”与“甜”构成存在主义的重量隐喻,暗合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对荒诞的诗意反抗,在日常琐事中淬取出存在的哲学密度,这种冷隽里面包含的炽热,呼之欲出,让你有如电击,为之一颤。
思想性:盐粒中的现代批判与重构
毛君娣的诗歌不仅停留于诗学表达,更有深刻的思想性,其核心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对替代性价值的探寻,有其精神上的追求和内涵,诗歌《白鹭》就明显带有上述特点:“从队列中出走,一只白鹭由此/打开它的精神窄门。/很快,它将长长的铁喙刺进湖心/翅膀指向天空,像指出另一种/活着的方式。//很快,它从大风里夺过/羽扇纶巾,一身素裹/攫住死神。//一只白鹭可以论证,我的身体里存在着/一种确切的死亡。或者说洁癖。”
很多人都写过白鹭,但一只白鹭,如何从众多的生理学上的白鹭,变成自己的白鹭,变成精神上的白鹭或者是那个被萃取出来的盐粒?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那个从队列中走出来的白鹭,就是她自己,是她替我们打开了精神的窄门,为我们指出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一只白鹭可以论证,我的身体里存在着/一种确切的死亡。或者说洁癖。”
毛君娣的写作证明:日常性并非诗意的对立面,而是其潜在的意义场域。她通过白鹭或者盐粒的意象,将历史记忆、现实批判与未来想象熔铸为一体,为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与参考的方法,这种既扎根于汉语传统,又融合现代反思的创作路径,也许可以为诗歌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