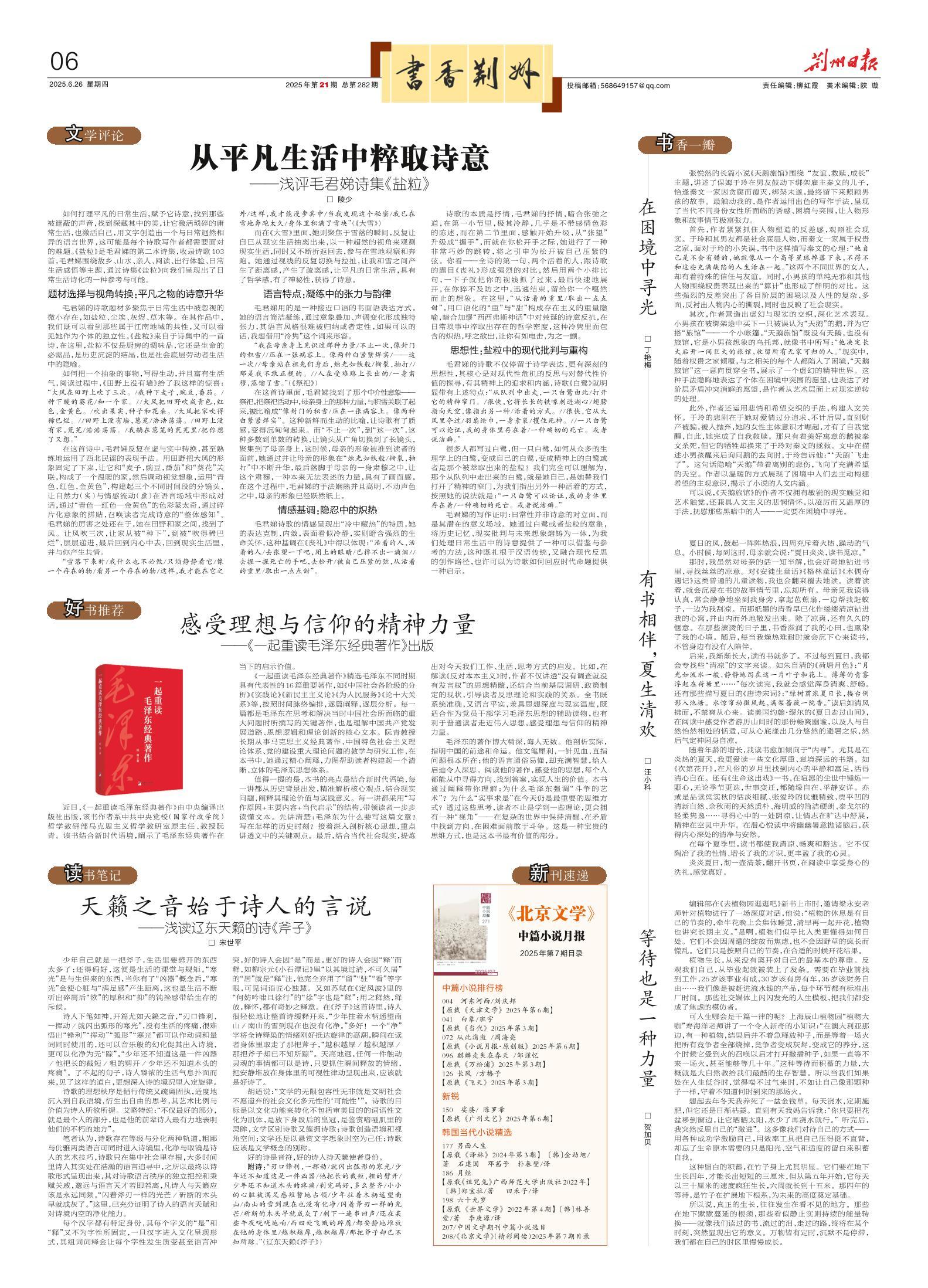□ 宋世平
天籁之音始于诗人的言说
少年自己就是一把斧子,生活里要劈开的东西太多了;还得码好,这便是生活的课堂与规矩。“寒光”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当你有了“凶器”概念后,“寒光”会使心脏与“满足感”产生距离,这也是生活不断斫出碎屑后“欲”的厚积和“抑”的钝挫感带给生存的斥候。
诗人下笔如神,开篇尤如天籁之音,“刃口锋利,一挥动/就闪出弧形的寒光”,没有生活的疼痛,很难悟出“锋利”“挥动”“弧形”“寒光”都可以作动词和量词同时使用的,还可以音乐般的幻化促其出入诗境,更可以化净为无“踪”,“少年还不知道这是一件凶器/他把长的截短/粗的劈开/少年还不知道木头的疼痛”。了不起的句子,诗人臻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见了这样的道白,更想深入诗的境况里入定旋律。
诗歌的理想秩序是循行传统又疏离固执,适度地沉入到自我语境,衍生出自由的思考,其艺术比例与价值为诗人所欲所握。艾略特说:“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
笔者认为,诗歌存在等级与分化两种轨道,粗鄙与优雅两类语言可同时进入诗境里,化净与取镜是诗人的艺术技巧,诗歌只在集中社会里存根,大多时间里诗人其实处在浩瀚的语言追寻中,之所以最终以诗歌形式呈现出来,其对诗歌语言秩序的独立把控和秉赋关戚,邈远与语言天才若即若离,凡诗人与天籁应该是永远同频。“闪着斧刃一样的光芒/斫断的木头早就成灰了。”这里,已充分证明了诗人的语言天赋和对诗境内空的净化能力。
每个汉字都有特定身份,其每个字义的“是”和“释”又不为字性所固定,一旦汉字进入文化呈现形式,其组词词释会让每个字性发生质变甚至语言冲突,好的诗人会因“是”而是,更好的诗人会因“释”而释,如柳宗元《小石潭记》里“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居”就是“释”注,他完全弃用了“留”“驻”“看”等字眼,可见词语匠心独慧。又如苏轼在《定风波》里的“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徐”字也是“释”;用之释然,释放,释怀,都有奇妙之释意。在《斧子》这首诗里,诗人很轻松地让整首诗缓释开来,“少年拄着木柄遥望南山/南山的雪到现在也没有化净。”多好! 一个“净”字将全诗释染的情绪刚好抵达旋律的高潮,瞬间在读者身体里取走了那把斧子,“越积越厚/越积越厚/那把斧子却已不知所踪”。天高地迥,任何一件触动灵魂的事情都可以是诗,只要抓住瞬间释放的情绪,把安静堆放在身体里的可视性律动呈现出来,应该就是好诗了。
胡适说:“文学的无限包容性无非就是文明社会不愿遗弃的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可能性’”。诗歌的目标是以文化功能来转化不包括审美目的的词语性文化为肌体,是放下身段后的皇冠,是鉴赏喑哑肌里的灵眸,文学区别诗歌又簇拥诗歌;诗歌创造语境和视角空间;文学还是以悬赏文字想象时空为己任;诗歌应该是文学概念的别称。
好的诗是音符,好的诗人持天籁使者身份。
附诗:“刃口锋利,一挥动/就闪出弧形的寒光/少年还不知道这是一件凶器/他把长的截短,粗的劈开/少年还不知道木头的疼痛/剁完码好,多么整齐/小小的心脏被满足感短暂地占领/少年拄着木柄遥望南山/南山的雪到现在也没有化净/闪着斧刃一样的光芒/斫断的木头早就成灰了/剩下一连串回声/还在某些午夜咣咣地响/而四处飞溅的碎屑/都安静地堆放在他的身体里/越积越厚,越积越厚/那把斧子却已不知所踪。”(辽东天赖《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