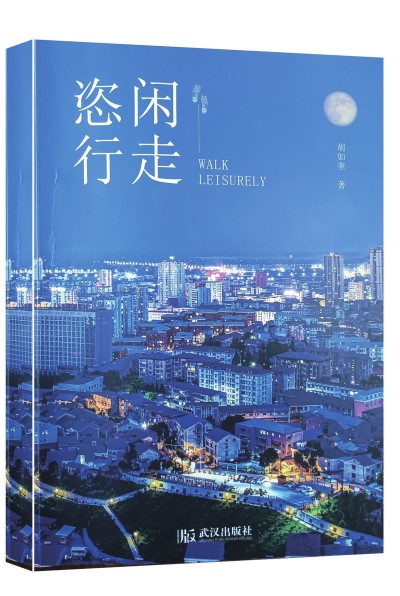□ 杨章池
《恣闲行走》是一部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胡如奎先生通过对脚下这片土、身边这群人、历年这些事,以及它们背后的历史沿革、文化渊源用心用情的观察、发现、整理、书写,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江汉平原的大致图景和一份“60”一代的人文切片。作品与作者气质一致,耐心、细致、平实、达观,老派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郑重敬惜的态度,驾驭文字时中正平和的书写,值得称道。我喜欢这本书中的“流连故乡”“漫步‘乐乡’”两辑,写荆州、写天门、写松滋的诸多篇章,情真意切,内蕴丰富,读后令人久久回味。
作者将所察所感所思娓娓道来,有时代的印记,又有个人的体温、气息。《我们的大荆州》,从游园博园入笔,汇入自己的生命轨迹,回顾与荆州交融的历史,作出了“一座城、一位神、一个人”的个性化归纳。《三棵树》是在写树,也是在写有风骨的皮影王、代表人性阴暗面的“汪代表”。《凿壁偷光》一文中写五七中学:“它仅存在十年时间,刚好是我老姐那一届进去扳砖烧窑做起来的,又刚好是我们这一届将其一砖一瓦捧着离开的——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吧。”融情于物,寄喟叹于时间,写尽了沧桑。在《不虚此行访小洲》中,他将冒甲洲与传说中的桃花源进行比对,肯定了它“打开了对外的门户”的开放之美,所以“地偏心不窄,心远地不偏”。《曾闻生灵向天歌》中作者对于“剁基尾”“伤了这生态圈的元气”的痛与思深沉恳切。
作者对于文化意义的追索和文学形象的塑造,既有探寻挖掘之劳,又有发现开拓之功。《我从乡间走过》中,对古县城新场的探访是一种田野调查式的文化抢救,文中对于古韵几何、农民几多、农事如何的思考,足见担当和胸怀。《乡愁》对徐苟三的评述发人深省:汪场人讲他的故事时把他安到黄坛,岳口人讲到他时就说是“蒋场有个徐苟三”,但都不把他“赶出天门”,诡谲滑稽。说明大家既推崇他,又怕受到某种“牵连”,揭示了一种微妙的集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松滋也有类似人物,“苏跛子修电筒——凭手艺”“王瞎子算命——照直说”的歇后语,及“祥德老汉”的故事,都广为流传。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畸零人”,介于聪明与疯癫之间,正常与乖戾之间,在直率和冒犯之间横跳。这即使算不上文学的创造,至少也是一种文学的思考呈现。《鸽王,鸽王》漫溢出一个逝去时代的苍莽雾气。
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作者语言功底扎实,文字表达简练传神、跳脱灵动。《乡愁情思下的与初小镇》有韵文、骈文的一些特点,兼具现代散文诗的韵味,对天人合一的那段描写特别有力。《好大的蜘蛛网》中跳句的运用很妙:“下午一点半,柚子扛回来了,不一会儿就满场金黄”,寥寥数语把人带到现场。《乡间武魂》写“朱义德放将”,写拜师“打艺”,趣味横生。他把传奇性寓于白描中,有笔记小说的隽永之味。他对“打艺”宗旨的概括——“打出强壮的体魄、倔强的性格、坚韧的毅力、高超的技艺、谦让的心态、正直的品德”,提炼出武术精神“体魄—性格—品德”的价值链。
这本书也展示了作者在审美发现、价值挖掘和文化品格探究方面的努力。《乡间食礼》看得我食欲大动,这是精神上的大快朵颐,也是文化上的温柔提醒。作者不揣繁缛的介绍,把我们领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简单、真诚的人际交往,朴素、热烈的时代风气作一次深情的回望。“十大碗”中每样食物都有它的寓意,超越实用功能进入审美和价值赋能层级,平凡的美好看似俗气,却承载日常的愿念,蕴含生活的本真。《外籍来客》中老闫那种“上善若水”“水无常形”,随意、随和、随性,既是智慧,又是高尚的品德,作者借此倡导当代社会舒适的相处方式,同时呼唤“放下”和“顺其自然”。
最后期待胡如奎先生在创作上能更深挖一层,更聚焦一点,更创新一步。书中部分作品已有可喜尝试,如《外籍来客》一文中老闫说:“这里的车站、公路、街道等好生地温和哟”,实际上是用多个视角来看松滋。再如《曾闻生灵向天歌》中作者写道:“记得是暖春晴朗的早晨,艳阳悬于门前的东南方,那个与我相隔一个‘花甲’的‘我’,正眯缝着眼,拎着小铲……滋溜一下就滑到了坡下。”此后即用第三人称来表达,以当下之我对于儿童时代之我实施观照,自我的爱怜贯穿全文,与对小生灵之爱交织融通,令人动容。对于如何进一步强化文体意识、设置多重角度、丰富文学表达,相信胡如奎有足够的底蕴,才华和智识去遂行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