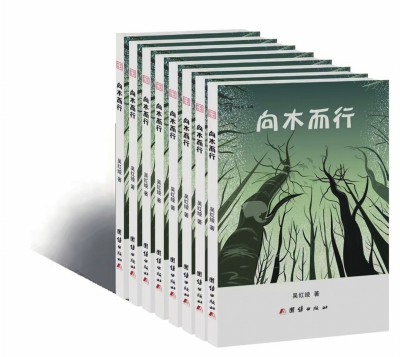□ 若离 朱必松
“大海有着天空一样的孤独/云朵有着鱼一样的孤独/我等待风暴/掀翻这些孤独/露出皮肉下倦曲的骨头。”(《孤独》)女性的孤独在本质上是同男性有着差异性甚至迥然不同的处境。
张爱玲曾经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以此来隐喻人生困境,强调女性在世态炎凉中需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通过对世情描写折射出女性对孤独与存在的哲思。
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核心观点,认为性别压迫源于社会结构而非生物本能。她指出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中容易陷入情感依附,呼吁通过独立思考和自我意识挣脱结构性枷锁,强调“女性的自由源于孤独中的自我创造”,孤独中的独立思考。吴红绫是具有独立思考潜质的女性,有时候也有江南女子撑一把油纸伞,漫步在三月樱花雨巷中的落寞和惆怅静寥的心绪。她的思想与她的性格,以及诗歌都有强烈的反差性,有着其自身的与众不同的辨识度。
“在海的远方,我拉低帏幕/悄悄蒙住星星的眼眸/只有我和你/只剩下我和你。”(《海的远方》)女诗人是天生的逐梦者,有着骨子里天性的浪漫和遐思。
“这个夏天/我伐木造舟,在蓝色的土地/种下千亩蓝荷/我追着星星跟着太阳奔跑/……我的肌肤一寸一寸暗了下来/剩下,眼睛雪亮/心无杂尘。”(《这个夏天》)
“离别的路上/谁揣着锋利的匕首/一刹那,那么疼,深不见底。”“一条鱼留在岸上/风顺走了它的呼吸。”(《一刹那》)
我认为,吴红绫这所写的才真正是海洋之诗,蓝色之诗。因为诗人把个人的感情同大自然的情感、同海洋的情感产生了共情和互动,这里有隐藏着的女性主义的身体哲学和身体欲望。这种欲望是压抑的,甚至是有着某种窒息感。
在当代女性诸多生存困境的层层挤压下,女性怎么样重新审视自我内心欲望与当代生活的关系? 女性怎么样从“身份焦虑”中实现自身突围? 也许,诗人无法给予答案和解药。
诗人擅长于把瞬间的情感倏然放大,产生一种悲情美学的氤氳氛围,晕染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吴红绫凛长于这一“伎俩”。
“滚滚尘烟从眼眸里消失/空空的手/拿捏不住一粒尘……/悲伤在每条褶皱里放大。”(《一刹那》)
读吴红绫的诗,像是在观摩一场水的“蓝色仪式”和“蓝色交响曲”。她的文字有一种湿润的质地,仿佛每个字都曾在蓝色的海水中浸泡过,带着盐分的结晶与潮汐的节奏。这二十首诗构成了一片蓝色语言的海洋,并且拥有琥珀色的金属阳光的质地。时而汹涌如“十万马蹄”踏浪而来,时而静谧如“海月水母”泛着银色之光。在这片水域中,我看到了两种永恒的姿态:一种是水的流动与变形,一种是石的坚守与承受。而在这两极之间,漂浮着无数渴望靠岸或远航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是让人回甘生津的。
水在吴红绫笔下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流动性以及象征性和隐喻性。它是《海月水母》中“跳进海里”的月亮,是《约蓝》里“倾入杯子的酒”,是《菊花回魂》中让干菊重生的沸水,也是《一刹那》中“咸苦淹死了鲜活的鱼”的泪水。这些水形态各异,却共同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重负。承载诗人对蓝色海洋的深情和对生活浓郁的热爱和眷恋。《菊花回魂》中凝视一朵干菊在沸水中舒展,她看到的不仅是物理的复苏,更是一种灵水在这里成为时间可逆的证明,成为前世今生连接的介质。
《石头的传说》中那个“上半身微倾向前”的礁石,是将军之妻的化身,她在海中等候夫君归来,“海老了,风旧了/她的姿势仍是最初的样子”。这石头不是无情的自然物,而是情感的纪念碑,它见证了“金戈铁马声声嘶鸣”,却选择以永恒的姿势对抗时间的流逝。
在《暗伤》中,诗人坐在爱人曾坐过的礁石上,青苔成为时间的见证者,“海浪轻轻地吻了吻我的脚踝”。这一刻,水的流动与石的固定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和解。“眺望远方,大海予我辽阔/我放过万物,为何放不下你?”水的宽容与石的执着,在这句诘问中形成了情感的张力。诗人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放弃执着,而是承认执着的价值;真正的辽阔不是无牵无挂,而是带着牵挂依然能够远航。
吴红绫诗歌中的海洋意象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万物源于水”的箴言。但在她的诗学宇宙中,水不仅是物质的起源,更是情感的源头,精神世界的滥觞。她在《海的远方》中构建了一个诗学的乌托邦,把女性主义的身份意识、身体性灼热的欲望、政治权力话语的“规避”、女性的道德困境、乡土社会伦理在时代的转型等等都进行了拟人化的纾解,也隐含着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权力结构不对等和政治话语权偏颇的反思。
吴红绫用这二十首诗建造了一个临海的居所,每个读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投影。也许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刻成为那个等待船帆归来的守望者,成为那块被海浪冲刷的礁石,成为那朵在沸腾的水中重生的菊花。而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我们:无论潮起潮落,无论帆远行还帆归航,生命的形态总在变化,但爱的能力永不枯竭,永远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在吴红绫的诗学宇宙中,水不仅是物质的起源,更是情感的源头,精神世界的滥觞。面对着这慌张而又混乱的现代世界,面对着诸多人类的不确定性,诗人强调个体灵性体验,依然保持着精神世界的高蹈期冀,且自身有相对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依附和盲从。她既有着对物质性的敏感,又有着一种骨子里不媚俗的“清新”“清洁”和“清贵”。自我营造出了一个想象中的海上“蓝色精神伊甸园”。既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虚拟性渴望。她对生命脆弱性的深刻认知,具有独特的洞见。认为,心灵创伤也可能是某种价值的来源以及自我精神性复活和存在的内生驱动力。
吴红绫在诗歌中告诉我们,生命的艺术不在于避免伤痛,而在于学会将伤痛转化为某种可以携带的能量而不致我们陷入于悲观主义的巢穴。
在吴红绫的诗歌中,我们仿佛还能听到远处的潮声。
仿佛能够听到张若虚那般在《春江花月夜》中的吟唱:“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大美之境和人间祥和的弘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