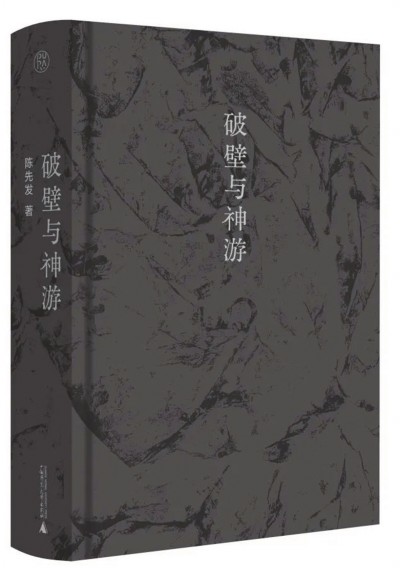口 陈进
陈先发 当代代表性诗人之一,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破壁与神游》,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草堂诗歌年度诗人大奖、英国剑桥大学银柳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22春季大赛翻译大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波兰等多种文字传播。
作为一位在世界诗坛具有辨识度的诗人,陈先发在创作与理论上均卓有建树,两者之间正好构成互证关系。选本《破壁与神游:陈先发诗文选》收录了陈先发从19岁至今创作的短诗、长诗、理论随笔与访谈,这并非只为收藏与致敬,更是一种叙事与建构,对其文学理念与风格进行强调与再凝练。这里,不妨以“破壁”为题眼,来管窥蠡测陈先发的诗作与诗学。
“破壁”在中国文化里寓意着置身困境之中的纠缠、酝酿与突破,蕴含着极大的精神力量,如同雷雨前的沉郁与闪电一瞬的突袭,要么积蓄磅礴的底蕴,要么获得瞬间的顿悟。先要理解“困境”,而后才能理解“破壁”。陈先发是一位具有极强困境意识的诗人,在他看来,“一切不凡的写作都与困境有关”“困境的起源,也是艺术的根本”。文学中的困境是一种趋同状态下的焦虑和创新意识的自觉。卓越的诗人都乐于寻求困境、制造困境,进而突破困境。先作茧自缚,而后破茧成蝶,唯有对困境的“破壁”,才能抵达诗歌的新境。
陈先发的困境意识首先在于对符号化现实的警觉,这也是他所要进行的第一重“破壁”。与真正的现实相遇,是诗歌之所以有诗性的根本所在。诗真正的困境,在于由现代科学的“脱域化”、专业知识的“概念化”、传统惯性的“符码化”构成的僵化语言秩序,将世人与诗人包裹其中,导致其无法与自我体认的现实相遇。正如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所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所以,“破壁”破的正是这一层僵化的语言秩序。诗人敏锐的天赋,当然会发现这一层无形之壁,同时,陈先发漫长的记者职业生涯也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新闻通讯中所有宏大抽象的概念与观点,都需要落到具体的人事上来体现。陈先发在《黑池坝笔记》中“对现实二字进行剥皮式的介入”,认为存在感觉层面的现象界,被批判、再选择的现实,现实之中的“超现实”,语言的现实这四个层面的“现实”。陈先发的这种对现实的体认与剖析,颇似柄谷行人“风景的发现”的理论范式。在柄谷行人那里,唯有在素颜的自然中注入内面意识,才能发现风景;在陈先发这里,也只有完成对符号化现实“破壁”的第一步,方能找到诗性的对象。
陈先发有首著名的诗歌《养鹤问题》,之前评论者多从诗人境遇隐喻的角度来阐释,却很少关注陈先发对“鹤”这一符号的“破壁”。“鹤”在传统文化中承载了过多的文化意义,乃至让人忽视其自然存在。“柱状的”“液态的”“气体的”“春泥的”鹤意在表明鹤作为一种文化性的符号,已经丧失了主体性,所以陈先发在《黑池坝笔记》里有段自我注解:“我们今天所见之鹤,作为一个符号在古时候就被掏空了。只为了证明时间流动的连续性,它的躯壳才被传递至今。鹤之上坐落着形式主义的最后殿堂。”
在《前世》里,陈先发将“蘸墨的青袍”“一层皮”“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云和水”“自己的骨头”一层一层的脱去,也是在破除梁祝爱情的种种文化符号,唯有“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的细节,和那一句简单到无以复加的“梁兄,请了/请了——”才是梁祝爱情中最纯粹的真实。那句“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既是真挚爱情对世俗偏见的对抗,也是诗心与“整个人类”构成的符号现实的抗争。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文化让位于实感;“碧溪潮生两岸”,具身涌动出符号。诗中层层脱去的符号,不免让人联想到陈先发在《黑池坝笔记》里所说的“诗学即是剥皮学”,他还说过“从河中跃出的每一条鱼,被剥皮后都是我”“伪经,剥皮后都是佛相”。“剥皮”并不恐怖,“剥皮”是“破壁”的另一种表达。
陈先发的另一种困境意识在于“影响的焦虑”,这就引发了他的第二重“破壁”。作为一位在桐城古城成长、过于濡染桐城派文化,又广泛精研过西方文学哲学的诗人,中西传统既是其宝贵的童年经验与精神资源,也是他不得不背负的文化负担。在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中,前人的巨大的诗歌成就可能使后人产生巨大的心理焦虑,而成为其创新途中的障碍。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里,令人信服的朴素文字似乎越来越难写;那些优美的朴素字句只能穿透诗的缝隙存在,犹如只能生长在山石裂缝里的植被。”在诗歌中追求传统性,或称古典性,对于当代诗人而言会凭空增添很多障碍。古典意象往往意味着已经承载了太多的传统意识,像一杯满杯的水,已经很难再注入新的个体性的情感。当诗人使用古典意象时,极有可能沦为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里所谓的“鹦鹉名士”。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说“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已变成后世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制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 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正是基于这种警惕,当代一般诗人极力避免诗中出现古典意象,转而谋求怪异奇诞,来为自我个体情感找到一块前人未曾涉足的“无人区”。蒋寅在对中国百年新诗研究后发现,像俞平伯、沈祖棻这些有良好古典诗歌修养,也有意发挥这方面长处的诗人,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就,反而是九叶派、“今天”派这些强烈排斥古典传统的诗人反而到达现代汉诗的最大成就。
但是陈先发与之不同,他似乎更乐意去这片历代文人开采接近耗竭的矿区冒险。他主动投身到伟大而又干涸的传统中。在他的诗歌中,古典的、农耕文明的、自然的意象明显多于现代的、工业文明的、城市的意象。对于传统的束缚,陈先发有两个看似正反相冲、实则辩证合一的态度。他很清楚传统具有黑洞般的吞噬性与同化性,但是在《黑池坝笔记》里他认为,“如何祛除这种影响的焦虑呢? 其实唯有一条道,就是忘掉文学史、忘掉什么古典什么后现代这些僵硬的概念、忘掉乱花缭眼的各类流派而一心精研自我的存在。”正是在这种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破壁”中,自我浸入并重建了传统意象,就像法国画家塞尚所言:“风景在我身上思考,而我是它的意识。”传统的意象在主客颠倒中获得了新意。曹操“月明星稀”之际的功业之心,化成《月朗星稀九章》里从日常生活、烟火人间抵达空明之境的玄径,李商隐寄北时的“夜雨”是孤寂与思念,在《脏水中的玫瑰》中化作自然之力与液态的生命本能,又变成《夜雨诗》里充满永恒感的时空信使。这便是“古今同一月,今古人不同”。在谈论《九章》的创作时,他又说:“个人写作应在一种严厉的自体约束中达到心灵的自由,就像在四壁封闭的斗室中去实现一颗心的无限漫游一样,以此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塑造。”这看似为自我施加艺术镣铐,实则是让“破壁”的通道更加清晰。正如法国学者马·法·基亚所说,艺术成规“与其说是缩小了作者的独创性,不如说是帮助说明了独创性”。也正因为如此,陈先发诗歌中那些明显的古典意象里融入当下时代的气质,和一个真正的、内面的自我。
在不断的“破壁”中,陈先发的创作显现出一条清晰的、可以分期的脉络。他自谓25岁之前是一种“无我”的状态,处于对经典的模仿时期,25岁之后进入“文学自觉的清晰形成”的“觉他”的状态,是“对一己之外的东西,对时代生活、对历史的认知在深化,也包含了语言本体意识的觉醒”。当然,“觉他”也就意味着“有我”,只有在和对象的相遇与凝视中,作为“我”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他还将自己的创作分为“带有青春期写作的心理特质,有深重的烈士情怀”的红色阶段、“诗歌美学和标志性形象”基本奠定的蓝色时期、“浓烈的个体情感正在淡出,一种缓慢而自醒的语调正在形成”的白色时期。卓越的诗人都会经历这样一层一层“破壁”下的自我精进与境界跃升。借助这本诗文选,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历时与共时交织、立体与阶段共存、困境与破壁相生的陈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