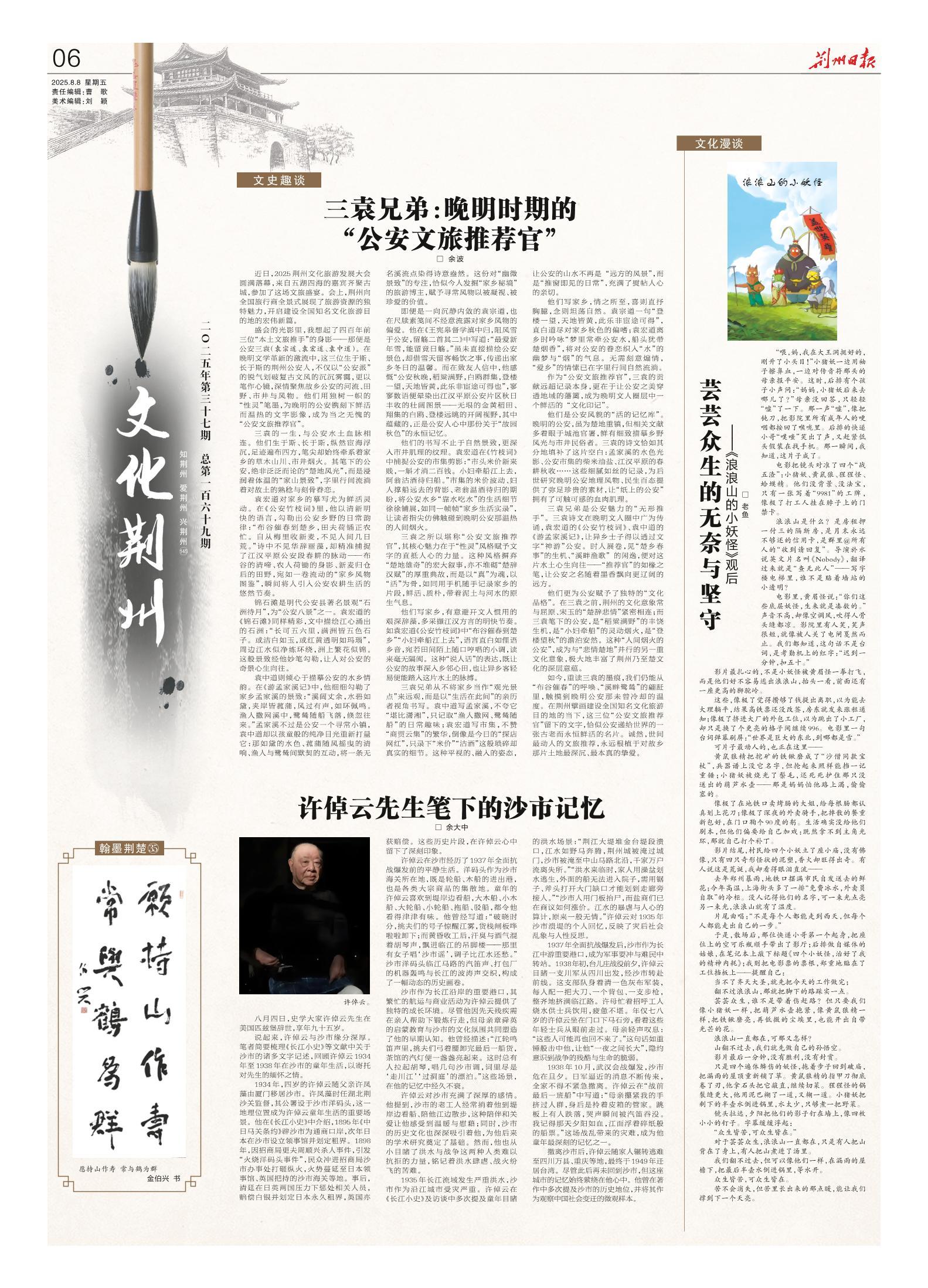□ 余大中
八月四日,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说起来,许倬云与沙市缘分深厚。笔者简要梳理《长江小史》等文献中关于沙市的诸多文字记述,回顾许倬云1934年至1938年在沙市的童年生活,以寄托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1934年,四岁的许倬云随父亲许凤藻由厦门移居沙市。许凤藻时任湖北荆沙关监督,其公署设于沙市洋码头,这一地理位置成为许倬云童年生活的重要场景。他在《长江小史》中介绍,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沙市为通商口岸,次年日本在沙市设立领事馆并划定租界。1898年,因招商局更夫周顺兴杀人事件,引发“火烧洋码头事件”,民众冲进招商局沙市办事处打砸纵火,火势蔓延至日本领事馆、英国把持的沙市海关等地。事后,清廷在日英两国压力下惩处相关人员,赔偿白银并划定日本永久租界,英国亦获赔偿。这些历史片段,在许倬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倬云在沙市经历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平静生活。洋码头作为沙市海关所在地,既是轮船、木船的进出港,也是各类大宗商品的集散地。童年的许倬云喜欢到堤岸边看船,大木船、小木船、大轮船、小轮船、拖船、驳船,都令他看得津津有味。他曾经写道:“破晓时分,挑夫们的号子惊醒江雾,货栈闸板哗啦啦卸下;而黄昏收工后,汗臭与酒气混着胡琴声,飘进临江的吊脚楼——那里有女子唱‘沙市谣’,调子比江水还愁。”沙市洋码头临江马路的汽笛声、打包厂的机器轰鸣与长江的波涛声交织,构成了一幅动态的历史画卷。
沙市作为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其繁忙的航运与商业活动为许倬云提供了独特的成长环境。尽管他因先天残疾需在亲人帮助下锻炼行走,但母亲章舜英的启蒙教育与沙市的文化氛围共同塑造了他的早期认知。他曾经描述:“江轮鸣笛声里,挑夫们弓着腰卸完最后一船货,茶馆的汽灯便一盏盏亮起来。这时总有人拉起胡琴,唱几句沙市调,词里尽是‘走川江’‘过洞庭’的漂泊。”这些场景,在他的记忆中经久不衰。
许倬云对沙市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提到,沙市的老工人经常捎着他到堤岸边看船、陪他江边散步,这种陪伴和关爱让他感受到温暖与慰藉;同时,沙市的历史文化也深深吸引着他,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也从小目睹了洪水与战争这两种人类难以抗拒的力量,铭记着洪水肆虐、战火纷飞的苦难。
1935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水,沙市作为沿江城市受灾严重。许倬云在《长江小史》及访谈中多次提及童年目睹的洪水场景:“荆江大堤堆金台堤段溃口,江水如野马奔腾,荆州城被淹过城门,沙市被淹至中山马路北沿,千家万户流离失所。”“洪水来临时,家人用澡盆划水逃生,外面的船无法进入院子,需用锯子、斧头打开大门缺口才能划到走廊旁接人。”“沙市人用门板抬尸,而盐商们已在商议如何涨价。江水的暴虐与人心的算计,原来一般无情。”许倬云对1935年沙市溃堤的个人回忆,反映了灾后社会乱象与人性反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沙市作为长江中游重要港口,成为军事要冲与难民中转站。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夕,许倬云目睹一支川军从四川出发,经沙市转赴前线。这支部队身着清一色灰布军装,每人配一把大刀、一个背包、一支步枪,整齐地挤满临江路。许母忙着招呼工人烧水供士兵饮用,疲惫不堪。年仅七八岁的许倬云坐在门口下马石旁,看着这些年轻士兵从眼前走过。母亲轻声叹息:“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句话如重锤般击中他,让他“一夜之间长大”,隐约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爆发,沙市危在旦夕。日军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全家不得不紧急撤离。许倬云在“战前最后一班船”中写道:“母亲攥紧我的手挤过人群,身后是拎着皮箱的管家。跳板上有人跌落,哭声瞬间被汽笛吞没。我记得那天夕阳如血,江面浮着碎纸般的船票。”这场战乱带来的灾难,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撤离沙市后,许倬云随家人辗转逃难至四川万县、重庆等地,最终于1949年迁居台湾。尽管此后再未回到沙市,但这座城市的记忆始终萦绕在他心中。他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沙市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微观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