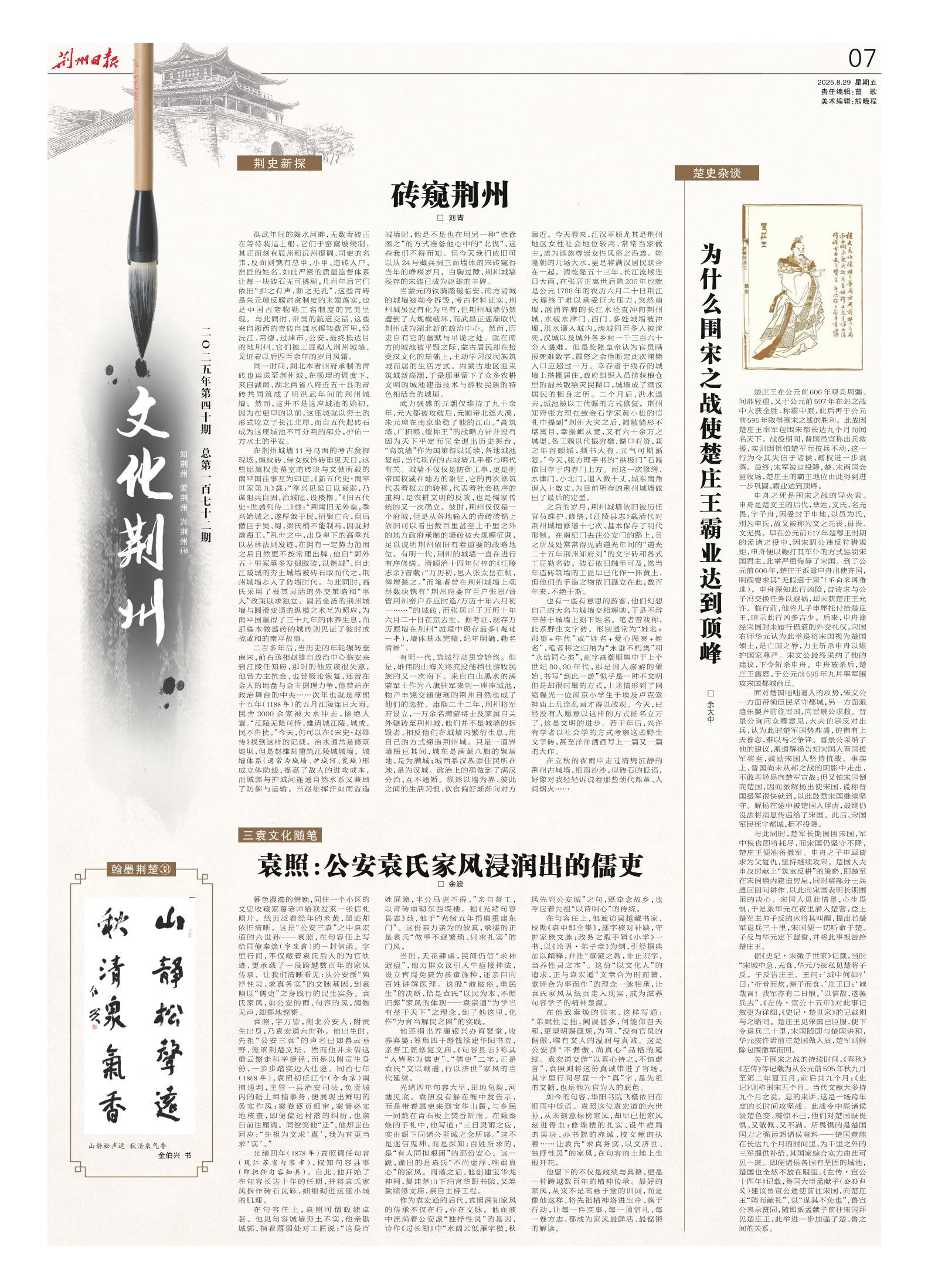□ 刘青
洪武年间的舞水河畔,无数青砖正在等待装运上船,它们于窑窿坡烧制,其正面刻有辰州和沅州提调、司吏的名讳,反面则镌有总甲、小甲、造砖人户、窑匠的姓名,如此严密的质量监督体系让每一块砖石无可挑剔,几百年后它们依旧“扣之有声,断之无孔”,这些青砖是朱元璋反腐肃贪制度的末端落实,也是中国古老物勒工名制度的完美呈现。与此同时,帝国的航道交错,这些来自湘西的青砖自舞水辗转数百里,经沅江、常德,过津市、公安,最终抵达目的地荆州,它们被工匠砌入荆州城墙,见证着以后四百余年的岁月风霜。
同一时间,湖北本省州府承制的青砖也运送至荆州城,在杨璟的调度下,来自湖南、湖北两省八府近五十县的青砖共同筑成了明洪武年间的荆州城墙。然而,这并不是这座城池的始初,因为在更早的以前,这座城就以夯土的形式屹立于长江北岸,而自五代起砖石成为这座城池不可分割的部分,护佑一方水土的平安。
在荆州城墙11号马面的考古发掘现场,绳纹砖、侍女纹饰砖重见天日,这些原属权贵墓室的砖块与文献所载的南平国往事互为印证。《新五代史·南平世家第九》载:“季兴见梁日以衰弱,乃谋阻兵自固,治城隍,设楼橹。”《旧五代史·世袭列传二》载:“荆南旧无外垒,季兴始城之,遂厚敛于民,招聚亡命,自后僣臣于吴、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乱世之中,出身卑下的高季兴以丛林法则发迹,在拥有一定势力范围之后自然更不按常理出牌,他自“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以甃城”,自此江陵城的夯土城墙被砖石取而代之,荆州城墙步入了砖墙时代。与此同时,高氏采用了极其灵活的外交策略和“事大”政策以求独立。固若金汤的荆州城墙与圆滑变通的纵横之术互为照应,为南平国赢得了三十九年的休养生息,而那些本做墓砖的城砖则见证了彼时或战或和的南平故事。
二百多年后,当历史的年轮辗转至南宋,前右丞相赵雄自政治中心临安来到江陵任知府,那时的他应该很失意,他曾力主抗金,也曾极论恢复,还曾在金人的地盘与金主据理力争,他曾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次年也就是淳熙十五年(1188年)的五月江陵连日大雨,民舍3000余家被大水冲走,惨绝人寰。“江陵无险可恃,雄请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扰。”今天,仍可以在《宋史·赵雄传》找到这样的记载。治水通常是修筑堤坝,但是赵雄却重筑江陵城城墙。城墙体系(通常为城墙、护城河、瓮城)形成立体防线,提高了敌人的进攻成本,而城郭与护城河连通自然水系又兼顾了防御与运输。当赵雄挥汗如雨监造城墙时,他是不是也在用另一种“徐徐图之”的方式准备他心中的“北伐”,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我们依旧可以从24号藏兵洞三面墙体的宋砖窥得当年的峥嵘岁月。白驹过隙,荆州城墙残存的宋砖已成为赵雄的丰碑。
当蒙元的铁骑踏破临安,南方诸城的城墙被勒令拆毁,考古材料证实,荆州城虽没有化为乌有,但荆州城墙仍然遭到了大规模破坏,而武昌正逐渐取代荆州成为湖北新的政治中心。然而,历史自有它的幽默与吊诡之处。就在南方的城池被平毁之际,蒙古居民却在接受汉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学习汉民族筑城而居的生活方式。内蒙古地区迎来筑城新高潮,于是那里留下了众多农耕文明的城池建造技术与游牧民族的特色相结合的城垣。
武力强盛的元朝仅维持了九十余年,元大都被攻破后,元顺帝北逃大漠,朱元璋在南京坐稳了他的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因为天下平定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高筑墙”作为国策得以延续,各地城池复起,当代现存的古城墙几乎都与明代有关。城墙不仅仅是防御工事,更是明帝国权威在地方的象征,它的再次修筑代表着权力的转移,代表着社会秩序的重构,是农耕文明的反攻,也是儒家传统的又一次确立。彼时,荆州仅仅是一个府城,但是从各地输入的青砖砖铭上依旧可以看出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的地方政府承制的墙砖被大规模征调,足以说明荆州依旧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明一代,荆州的城墙一直在进行有序修缮。清顺治十四年付梓的《江陵志余》曾载:“万历初,邑人张太岳在朝,俾增甃之。”而笔者曾在荆州城墙上观得数块镌有“荆州府委官百户张恩/督管荆州窑户乔应时造/万历十年六月初一……”的城砖,而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在京去世。据考证,现存万历原墙在荆州“城垣中现存最多(超过一半),墙体基本完整,纪年明确,勒名清晰”。
有明一代,筑城行动贯穿始终。但是,雄伟的山海关终究没能挡住游牧民族的又一次南下。来自白山黑水的满蒙军士作为八旗驻军来到一座座城池,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荆州自然也成了他们的选择。康熙二十二年,荆州将军府设立,一万余名满蒙将士及家属自关外辗转至荆州城,他们并不是城墙的拆毁者,相反他们在城墙内繁衍生息,用自己的方式缔造荆州城。只是一道界墙横亘其间,城东是满蒙八旗的聚居地,是为满城;城西系汉族原住民所在地,是为汉城。政治上的确做到了满汉分治、互不通婚。纵然以墙为界,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渐渐向对方靠近。今天看来,江汉平原尤其是荆州地区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常常当家做主,盖为满族尊崇女性风俗之沿袭。乾隆朝的几场大水,更是将满汉居民联合在一起。清乾隆五十三年,长江流域连日大雨,在张居正离世后第206年也就是公元178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日荆江大堤终于难以承受巨大压力,突然崩塌,汹涌奔腾的长江水径直冲向荆州城,水破水津门、西门,多处城墙被冲塌,洪水灌入城内,满城四百多人被淹死,汉城以及城外各乡村一千三百六十余人遇难。但是乾隆皇帝认为官员瞒报死难数字,震怒之余他断定此次淹毙人口应超过一万。幸存者于残存的城墙上搭棚居住,政府组织人员捞获粮仓里的湿米散给灾民糊口,城墙成了满汉居民的栖身之所。二个月后,洪水退去,城池被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复。荆州知府张方理在致金石学家黄小松的信札中提到“荆州大灾之后,凋敝情形不堪寓目,幸振衈从宽,又有六十余万之城堤,各工赖以代振穷檐,餬口有资,兼之年谷顺城,频书大有,元气可期渐复。”今天,张方理手书的“拱极门”石匾依旧存于内券门上方。而这一次修缮,水津门、小北门,退入数十丈,城东南角退入十数丈,为目前所存的荆州城墙做出了最后的定型。
之后的岁月,荆州城墙依旧被历任官员维护、修缮,《江陵县志》载清代对荆州城垣修缮十七次,基本保存了明代形制。在南纪门去往公安门的路上,目之所及处常常得见清道光年间的“道光二十五年荆州知府刘”的文字砖和各式工匠勒名砖。砖石依旧触手可及,然当年造砖筑墙的工匠早已化作一抔黄土,但他们的手造之物依旧矗立在此,数百年来,不绝于斯。
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游客,他们幻想自己的大名与城墙交相辉映,于是不辞辛苦于城墙上刻下姓名。笔者曾戏称,此系野生文字砖。形制通常为“姓名+郡望+年代”或“姓名+爱心图案+姓名”,笔者将之归纳为“永垂不朽类”和“永结同心类”,刻字高潮期集中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是国人旅游的肇始,书写“到此一游”似乎是一种不文明但是却很时髦的方式,上述情形到了网络曝光一位南京小学生于埃及卢克索神庙上乱涂乱画才得以改观。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扬名立万了,这是文明的进步。若干年后,兴许有学者以社会学的方式考察这些野生文字砖,甚至洋洋洒洒写上一篇又一篇的大作。
在立秋的夜雨中走过清隽沉静的荆州古城墙,细雨沙沙,似砖石的低语,好像对我轻轻诉说着那些朝代鼎革、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