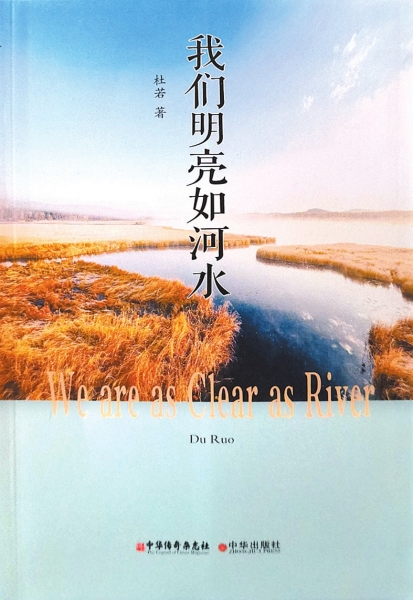|
||||
|
||||
|
垄上诗评 □周卫刚 — 作者简介 杜若,本名杜丽君,湖北松滋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作协会员。诗作散见于《华语诗刊》《诗歌周刊》《天津诗人》《武汉作家》等书刊。有作品入选《湖北作家作品选》《湖北基层文学丛书#·荆州散文诗歌卷》《荆州当代诗百家》。曾获王夏子文学奖诗歌一等奖。出版诗集《涓涓之水》《我们明亮如河水》。 在松滋诗歌界,杜丽君老师可谓创作丰硕,继第一本诗集《涓涓之水》之后,近期又出新诗集《我们明亮如河水》。 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其物质精神构成及其内在规定性并由此搭载它的创作者抵达永恒和不朽,每一位艺术家都必然借由遵守其物质精神构成及其内在规定性方能创造出抵达永恒不朽的作品。从分析解读杜丽君的诗歌作品看,诗人抵达永恒和不朽的路径探索可以说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在对抒情主体的形象塑造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注重抒情而不太看重叙事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杜丽君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其绝大部分作品都归属于形制精美的抒情诗。这些形制精美的抒情诗,其艺术价值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价值成就是初步完成了对于一个特定抒情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这一抒情主人公可以说是生动灵秀,性格独特,内心丰富,温婉柔情,多愁善感,沉静明丽,善解人意,细腻忧伤,典雅知性,让人赞美欣赏,让人难以忘怀。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会因诗而立,因诗而传,会和诗一起抵达永恒和不朽。 《如果,真的爱过你》与其说是一首抒情诗,不如说是诗人用诗歌形式为现代社会理想女性提供了一个写意标本:内涵、纯情、沉静、温柔、坚韧、宽广。和这首诗一样,还有很多诗都在抒情达意之中从不同的方位角度和层面丰富完善了对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这一形象塑造已经很成功,已经卓然独立。有读者读了杜丽君的诗之后,误以为诗人还是一位纯情少女。杜丽君自己也说:因为诗,“很多这之前不认识的人,都有误解我年龄的发生,我除了粲然一笑,只能告诉你,是诗歌缔造了另外一个我,如同年轻的风浩荡原野,让人始料不及,也让我对自己平生第一次刮目相看。”正因为诗中有了这样的“另外一个我”,有了诗中的这样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不管社会生活中的诗人实际年龄如何,日子过得咋样,诗和诗人都必将在路上向着永恒和不朽不断靠近。 在对特定意境的精心铺设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诗歌以意境传情,读者以意境入情。意境即情景交融,即意象互生互指。大学问家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诗亦如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杜丽君是深谙此道的,绝不会枉费笔墨,其诗歌之有境界自不必言。要说的是杜丽君的诗歌意境是特定的,是与众不同的,是精心铺设的。一方面是以特定女性视角、恋乡情结、忧郁天性、善良多梦等主观之情导引选取相应的具体事项物象,精心酝酿构筑自己的诗歌意象。故乡、老街、父亲、生母、继母、哥哥、妈妈、恋人、篱笆、炊烟、特别是柳林河,还有很多很多的日常小事一草一木,都成了诗歌中有故事的主角,都成了诗人的寓意之所,寄情之物,都成了诗中的达意之象。另一方面是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功底,对古典诗文意象进行拿来、解构、运用,按照新诗的要求构建新诗意境。诗人刘盛云在《古典诗境中的温婉情怀》一文中说:“杜丽君女士的诗作形制精致,韵律鲜明,意象丰富而深远。她的诗几乎都在十五行左右,然而尺水兴波,千帆旖旎。她擅长从古代经典中拈出诗性元素,诸如一丛蒹葭,一段落霞,一截东篱,一剪寒梅,一弯霜月,一支雁翎,一场初雪,机巧地加以移植或融合,使之化为自己诗意中的多肽,并滋长成为一片动人的风景。” 在对读者受众的选择期待中抵达永恒和不朽 读过诗人的第一部诗集《涓涓之水》,再读过刚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我们明亮如河水》,我觉得诗人的创作对于读者受众的期待是有选择的,并没有期待很多人都能读懂她的诗喜爱她的诗。她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感受思虑,玄远而幽独,即便是用散文的方式面对面地诉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懂。在意象的铺设中大量使用比喻,特别暗喻隐喻和象征借代,让对所涉对象的物性物理和情感寓意不熟悉的人进入诗境有一定的难度。在当下生活节奏加快,文化供给快餐化的今天,亲人之间在时间陪伴尚已成为奢侈,让一般的人花很多时间,通过读诗来陪伴我们诗人,更应该是一种奢侈。但没有关系,人类不能没有哲学家和诗人,生活不能没有诗和远方,诗总会拥有读者,读者总会需要诗。只要诗歌创作坚持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就一定能够抵达永恒和不朽。 杜丽君的诗大部属于新诗,而新诗的正式诞生也不过40余年。对于新诗的相关问题,我曾于2008年在《凤凰城读诗》表述过一些想法,现引用到这里供参考并祝福杜丽君在康居快乐中有第三本和第四本诗集联翩出版! “面对新诗读不懂,没人读,不能打动人,写诗的人也徬徨迷惘的情形,面对新诗就是写句子加回车等新诗理论,我和身边的诸诗人曾不止一次地探讨过新诗的特质问题。就在去凤凰城的路上也还在讨论,试图找到答案。读了黄永玉先生亲手书写的诗,我坚定了自己对于新诗的几点理解:首先是诗贵有情,有真情,有深情,有激情,有‘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共有之情,就像黄先生诗中所表达的对故乡的情。其次是诗的语言并不需要晦涩朦胧,而是越明白的话越好,越直接简单越好。就像黄先生的这首诗,没有哪一个词句需要用心琢磨思量的,所有的语言就像为我们进入黄先生心灵情感世界专设的直通车和康庄道。所以写诗不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不是让语言成为门槛,不是要在诗人和读者的心灵之间设置隔离障碍,而是要架设宽敞平坦的桥梁通道,最好是让诗人和读者的心灵直接相通相连,也就是要做到王国维先生说的‘不隔’。其三是,诗是写给有情的人读的。有情的人自然会喜欢诗,自然会有幸读到很多的好诗,无动于衷的人不容易喜欢诗,也是很难读到和读懂好诗的,所以不要期待所有的人都成为诗的读者,在娱情娱心多样化快餐化的今天,没有必要为读诗的人数不那么多而感到伤心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