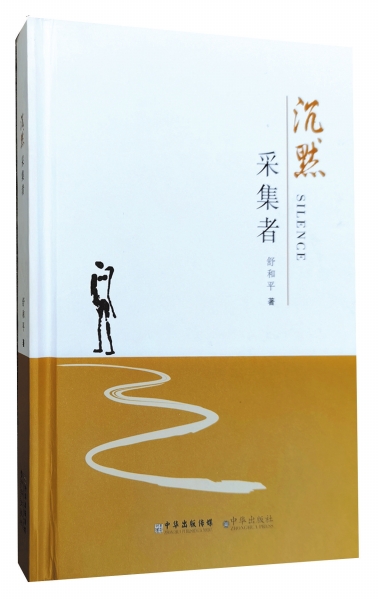|
||||
|
||||
|
□杨章池 垄上诗评 当你多年后回首,会发现在熟悉的一切面前你已经成为陌生人,这不仅仅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时间错位,更有情感在时空共同作用下的沉淀和发酵,含着愁绪也带着解脱,被伤怀洇染也被光阴慰藉。《沉默采集者》就是向你端出的这份“怅惘”——如同从岁月深处发出的一声喟叹,充满留恋、不舍,饱含着守候的情义和贴己的关怀。 我坚定地认为,怅惘,是诗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这是一种向来处回溯的“刻舟求剑”式的张望;“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一种时光淘洗不掉的刻骨情凝;“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是一种致敬美好的无奈相思。与之相类似,舒和平呈现他与生命中“亲切的关联”的方式是站在当下的视角,对过往一切投注即刻的观照,从而使所述之物获得一种足以产生陌生、错位、失落、怀念、迷茫的可贵距离。“我刚从乡间的斜坡上下来/就遇上虚拟的时代/舞台和角色离我很远/我只是个陌生的问路人”(《经过》),这样的自我定位,我觉得是诗人有异于庸碌凡人的一种隐喻。 平实而内蕴丰富的书写让“惆怅”透于纸背。舒和平的书写中,故乡、血缘、亲情占了很大比重。“习惯了重生薄死的我们/只有在这一天,才会把/前面断裂的骨头/从后面接起……”(《清明之诗》),“此刻,一串记忆的猴子/倒挂在大树上/替我打捞精美的钥匙”(《老屋》),这里面,有对于命运的感恩与思考,对于传承的尊重和礼赞,而且大都脱离了简单的咏物抒情,从被一遍遍无效摹写的固化模式中走出来——我多次叹息,当代诗歌有太多的人云亦云的“大实话”和不知所云的“鬼话”,从被过度开采的不多意象中搜刮剩余价值,本就无价值。而舒和平以坚实的文本“锚住飘移的土地”(《母亲择水而居》),系列作品表现出了沉潜之力、沉淀之美和沉郁之气。当然,他的丰富性体现在情感维度的多元:如《推石头》中岁月的阴冷和母亲的孤寂,《父亲与草》的荒凉,《乌龙》的疼痛。除此之外,舒和平还将温情的眼光放大,以温情的目光触摸、爱抚他周遭的人、物、事:松滋河,太平村,工棚,护林人,拾荒人,吹肥皂泡的老人,棺材匠,打工者,给予他们清晰的面目……那一场场重逢,那一番番夜里的思量,一回回还乡,一次次那在现实与回忆中叠合又交错的老街,如一幅幅岁月的素描,在诗人的捕捞和刻画中获得了永生。 倾向于“旧”的审美表达让“惆怅”闪闪发光。一是直接写“旧”。这里面有多少美好,就有多少不甘和不舍:“就像不知深浅的风/起青萍之末,未曾站稳/就一脚滑进了秋天”(《初恋》);物是人非中饱含对光阴的留恋:“一张30年前的旧船票/把我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多少雕栏玉砌变更为/涂上了朱颜的石头”(《桑梓》);在“界碑与墓碑”前与古典相逢:“在干枯的笔墨,重又/温润之前,空山在说话/流水在说话。我也借杯中的/明月,说说草木本心”。对“信”等旧物的追忆中也有对网络时代的温和的批评,“几案和木椅是必须的/我把信札定位在新河山或旧情人/还有那从键盘里救出的草书似的签名”(《信》)。“以旧换新”,或直陈当下事物中“旧”的部分以为起跳之基:“泛着绿锈的铜钉/铺成一段够不着的路/十九级阶梯/让沉重的事物,越走越轻”(《章华寺》),或自我“旧化”以完成更深沉的观照:“此刻,我正以青苔的目光/凝视它不完美的裸体”(《石头》),即使是当下场景如《春运》,也带有某种“回忆”的气质。《余生》写退休(“从锃亮的铁轨上下来/我的身体已经变旧”)生活,仍不失敞亮与豁达:“好在稼穑补山/星光是露珠的/我俯身向下,只取一滴/与之相互照映”。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简单地说舒和平采用了回忆的视角,倒不如说,经过时间和情感的双重发酵,诗人的书写因遥远而厚重,因更纯粹的烟火之气而驰骋于人类“共情”的疆场。 出色技艺让“惆怅”获得生命。变形、陌生化,对意义的抽剥和反转,让语词在延宕与滑行重获生命,对这些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人运用得游刃有余:“蒙在竹筒上的蛇皮,比蒙在鼓里/靠谱”(《二胡》),“花吞没了蜂,但蜜被嗡嗡地借走”“我梦到自己,同声传译/整个江汉平原,像金碧辉煌的大教堂”这样的神来之笔并不少见。我再列举《练习本》这一组散章中的一些句子:“你顺手牵走的羊/露出了马脚”(《马脚》),“被秋后算计的/蚂蚱,拴在夏天的绳子上”(《蚂蚱》),“大片大片的麦田/在骚动的乌鸦/和梵高之后/绝尘而去”(《流失》),“昨夜写下的/——露珠/晃动在鸡鸣鸟翅上”(《晨曲》),“月光是雅各的梯子/让我们落入天空的牢狱”(《宿命》),“石头孵出的泪水/一滴背井/一滴落在还乡的路上”(《乡愁》),等等,足见诗人非但宝刀不老而且日益精熟。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指责诗人对创作态度的油滑或轻浮,恰恰相反,在多年来的交往中,舒和平那种倾心于诗又无求于诗的旷远和自洽给荆州诗歌圈带来了正面积极的影响。话说回来,常人写诗,有时候是不是过于庄重过于形式化,正襟危坐苦心孤诣常常带来“目的性颤抖”,而笔由心走、无拘无束、信马由缰有时却能歪打正着地达到好诗。就看你怎样把握这个“度”。作为怅惘的象征和寄托,月亮这一意象曾被无数古今中外的诗人所吟咏,我们拿舒和平笔下的“月亮”这一意象来看:它有时候表现为一种过尽千帆后的宁静:“我在车灯和马灯之间飘移与往返/问大数据,过小日子/又见一轮明月,落在/今夜的砚池中”(《月光曲》),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时间之伤:“还沉醉在惠山泉边的阿炳/不知道今日,依旧的一段长弓/就把荆州城头,如丝如扣的/月光,拉得遍体鳞伤”,有时候表现为时空交错中一个恍惚的瞬间:“一条河穿过钟声/穿过我们。我站这里/夕阳滑落时/她提来一桶月亮”(《还在》)。这说明,即使对于同一事物,有时会取它这一属性,有时则取它另外的属性。但不管怎样,只有以强烈的主体人格投射进去,才能获得其独特性,而独特性,恰恰就是诗歌的有效性。 适度的抽象和空茫让“惆怅”稳稳落地。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毕竟抽象、空茫、惆怅都是虚,但且慢,诗歌从来不缺少化虚为实的手段。看看竹篮:“韧性十足,又含情脉脉/从来就没有空过/即使打的是水”(《竹篮》),这就超越了许多人,思辩甚至“哲思”的层面。看看仙人掌:“仙人掌性寒、味涩/能清肺、健脾、养颜和疗伤/我们不是本草,却互为/良药”(《仙人掌》)。这段释义瞬间拉开实物的距离,赋予其文献学的意义,也无形地深化了主题与诗意。“叶子在落,一直在落”,平静的陈述,忠实地传达了生命流逝的痛感。还有,“我”抽离“我”,“物”“我”相融:“不远处,一条抛开石头/光屁股行走的小河/是我的好声音”(《白夜》)。诗人认可这种神秘:“生命中有些音符/是碰不得的”(《钢琴独奏》)。面对背负的太多,诗人认为:“不如一醉归零/把自己虚进去,空出来”(《清理》)。一阵落花风,云山千万重;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已经年过花甲的诗人,对于“逝者如斯夫”的光阴是有发言权的,谢天谢地,年华老去时审美让逝去的光阴重回,带着被濯洗、打磨后的光泽。这时,怅惘,表现为一种空茫:“而松针和时针都很慢,慢到/我在目击温水与青蛙的对视中/苟活了许多年”(《空山》)。佛家有一苇渡江的故事,诗人也可以借一件小小的事物腾起,重新获得力量、勇气和希望——看看《赏梅》中诗人与小孙女的交流:“昨夜,她梦见梅花了/它把闯入她梦境的卡通鹿/驯化成一只梅花鹿”,对岁月伤逝逐渐变得淡然,童心介入,可以是点化甚至是救赎。 诗人,包括一切写作者、艺术创作者,其创作过程无不带有个体生命的、情感的特征,有的强烈有的淡,有的跃然纸上,有的引而不发。舒和平在长时间的写作中追求和践行的这种怅惘诗学,正日益沉淀为具体可感的特质。近期诗人的写作更增进了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的沉稳、从容。当一位诗人不得不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陌生的问路人”正在“努力撷取明亮的东西”(《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