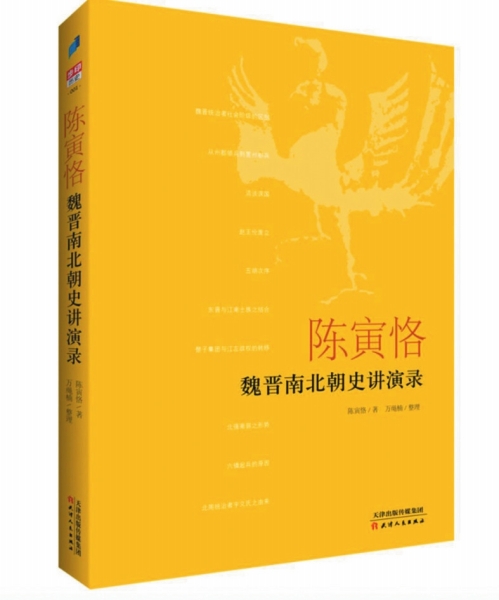|
||||
|
||||
|
□陈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迷人的时代,一个名人辈出的时代,一个让后人崇拜的时代。魏晋风流,在学者们的眼中就是谜一样的世界,而陈寅恪先生的讲稿正是我们厘清它的利器之一。 严格意义上说,《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这本书不是陈寅恪的著作,是陈的学生万绳楠在1947年至1948年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期间,听陈寅恪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的笔记。笔记通常是简略的,为整理成书,万绳楠参考了陈先生讲史时引用的史料,以及不少专业论文。虽是转述加工,大体是陈寅恪史学成果的一次凝炼,显示出陈寅恪在史学上极高的见地与敏锐的眼光。 学者周一良回忆陈寅恪先生,说他最大的了不起之处是在“打通文史哲”,达到了人文科学的化境。因为文史哲的打通,使得陈寅恪先生能提出许多“在我们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崭新论述。例如西晋灭亡的原因很多,如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九品中正制的弊端等都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因素。但陈寅恪先生通过对纷纭的历史现象进行详尽分析,指出:“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至巨。”因为晋武帝罢去州郡兵,州郡只有武吏,而封国的军队仍存。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国属于诸王。诸王一旦发动战争,朝廷将无法控制。“八王之乱”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很强大。鞭辟入里地揭示出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读完后真有种庖丁解牛的快感。 同时,陈寅恪先生在小处亦有洞见,各种判断,引经据典,皆有出处,皆能对照。如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考证,指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虽在南方的武陵,但不能对其地理信以为真,其纪实成分当来自南朝北伐时戴延之记录下的北方坞堡。北方坞堡是在五胡入华的战乱背景下,一些大宗族依托险要地形,建起保卫安全、传承文化的要塞。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载了他寻访过的几个坞堡,而陶渊明又与当时西征将佐颇有关系,故陈寅恪先生疑陶渊明乃是直接或间接地得知戴延之等人的经历,遂纳入《桃花源记》一文中。他还指出,《桃花源记》提到的为逃避“秦”的暴政,实际上不是秦始皇的秦,而是当时北方的前秦。最后,先生得出结论:“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潜思想的反映。”文史互证,抽丝剥茧,就如陶渊明笔下那个渔夫,让人有豁然开朗、另有天地之感。 陈寅恪先生治史的高明处在于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史料的丰富倒在其次,看《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材料虽然细密充实,但引证所出不过《晋书》《名士传》《世说新语》等几部常见的史籍,未见什么独得之秘。,其精到在于融汇、对比和分析。对材料的取舍和分析,最能见一个历史学家功力的深浅。读完全书,更觉得先生最终没能著成《中国古代史》那样的皇皇巨著,殊为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