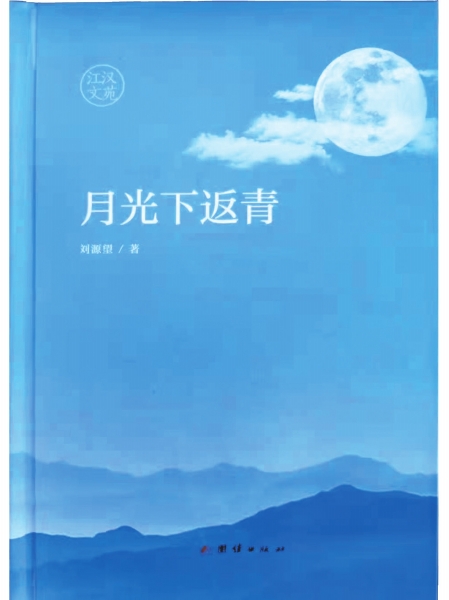|
||||
|
||||
|
□朱必松 刘源望诗集《月光下返青》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洪亮的声音》、第二辑《月光下返青》、第三辑《自然的园艺》。 刘源望是我身边的诗人。他仿佛是一支冬笋,充足地吮吸了大地的养分、阳光和碳水化合物,厚积薄发、破土而出,葳蕤地生长,并逐渐长成了一颗枝繁叶茂的“诗树”。 亲历的真实性点燃了他诗性的生命激情 刘源望诗歌的第一次“井喷期”是在抗疫期间,他作为湖北省应急厅的一名公务员,是真正地投入在抗疫第一线。他的“在场感”能够把“抗疫诗”写得入情入理、入心入肺,体现了他后天意识形态领域学习中的启蒙、理性、责任、担当等信念,这种诗歌也可能是为历史存照的一部分,是处在特殊生命时空中的一种朴素的苦难记忆和抒写。 “没一天不在秣马厉兵/没一刻不在随时准备出击/应急,这两个字早已溶进了我们的血液/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更是倾尽全力/虽不是在前方与病毒短兵相接……我们有时也伤痕累累/有人称我们是逆行者/有人说我们是急脾气/其实我们也是战士/虽然手上没拿武器/但我们的名字叫——应急(《我们的名字叫应急》) 诗人说:因为武汉这次疫情,让他作为一个在武汉城内的,又是参与了这个工作其中的人,目睹了很多事情,激起一个曾经的“乡下人”对生命进行重新思考。诗集《月光下返青》是诗人写给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明天的诗篇。有细节、有情节、有温度、有人性、有担当,能够凝聚一座城市爱的力量,我们把这种力量叫精神或说是信仰,诗人用诗歌把这种爱的力量传递、传承、传播,这本身就是一种大美和大爱,就是一种担当和情怀,也就是一个诗人要为人民和时代写作的精神旨趣和理想抱负。 烂熟的岁月之窗,总能喷出新的火焰 在第二辑《月光下返青》中:“从人、从、众里、找到了三生万物/从大、天、夫里,找到了肩,找到了谏/在星星调皮的眨眼里,无形,有形/烂熟的岁月之窗,总能喷出新的火焰。”(《岁月能读懂的诗》) 在这首诗中蕴涵了一定的逻辑关系,有一种诗之思的哲学秉承,在一种递进式的关系中,喷薄出一种诗性的火焰。 “母鸡被家暴得浑身发乌/赌气,生了个绿蛋/不曾想声名远播/落寞的公鸡耿耿于怀/每天,天还没亮就鸣不平。”(《绿壳蛋》) 现代人到底是逃离还是无处可逃?似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巨大隐喻。这首短诗虽然只有六行,但实现了一次突转,并且在第二次突转即将来临之时戛然而止。这在诗歌技术上己趋于圆融和成熟。它并不是诗歌修辞或词语意义上的空转,而是揭示了一种微小事物的性征和反抗。 “我越来越不喜欢轻易的表现/只有金黄色的东西我才在意。”(《绿色里藏着一片黄叶》) 诗人的乡愁是需要被重新定义的。“夏天的过云雨,不知道悯农隔三差五,都是这样……”从一个特定的细节和意象让《晌午》一诗生动起来。《风电》《锣》这2首短诗截取的横断面都有新颖之处,使其捕捉生活细节。如果说《绿色的比喻》是诗人《乡愁,最绿色的比喻》这首组诗的压轴之作,毋容置疑,对中国的乡土经验和中国故事的讲述上,是暖色调的。自然性、地域性与时代性和人性进行了同构,既有对过去的追忆,又有对当下的警醒和思考,更有对未来的憧憬。 对土地的深情长成了“情瓷” 在第三辑《自然的园艺》中,“悬崖峭壁上/迎着风雨的古树/都是佝偻着的/歪歪倒倒/甚至,缺胳膊短腿/顺势是为了更坚固的站立/自然的园艺/并不在乎光鲜的千篇一律”(《自然的园艺》) 这种思考富有洞见。 “肉搏后,也分不清旧疤新痕/每被动配合施虐一次/伤口至少得用一个晚上挂着来舔”(《砧板是最憋屈的第三者》)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博弈的在场,有着某种精神性谱系的陈述,这是一种与乡土血脉和乡村伦理有着关联的语言迷宫。 “有时定量,有时定性/有时量一次,有时量一生。”(《尺子》)这富有生活的辩证法,将具体的微小事物升华为道德和人格的箴言。 诗人的内心是有谦卑与诚实这两个品相的。他把思维的两个触角,不断在城市和乡村两个场域转换,这肯定是一种至为珍贵的禀赋。城市生活经验和乡土中国记忆支撑了刘源望精神世界的两个维度,使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宽阔与丰富,以及诗人内心的波澜。 在这本《月光下返青》的诗集中,让我读到最感动的一首诗是《娘》: 娘,苍天般的大爱/成就了天底下最美的娘 在这首诗的叙述中,前后充满了矛盾性,也是人性的善恶在心灵世界的交锋,正是这种歧义性和其矛盾性,实现他心灵世界的巨大反转,正是这种东西,让他的思维世界慢慢长出了,对故乡对母爱的“情瓷”。 如果说刘源望的诗歌中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如果能够更多融合异质文化的多重性,在“历史的单元”叙事和“西方哲学”思维中再下些功夫,完全可以更大幅度地提升其整体诗学的精神品格,这是所有读者和批评家对他更高的期待。 其实,人生的春天就只是需要挂一枝芦花,就可以找到美好的春天,抵达到春风荡漾的世界。 (刘源望,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现居武汉。湖北省作协会员。诗歌、散文散见于《诗刊》《长江丛刊》《芳草》《中国诗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