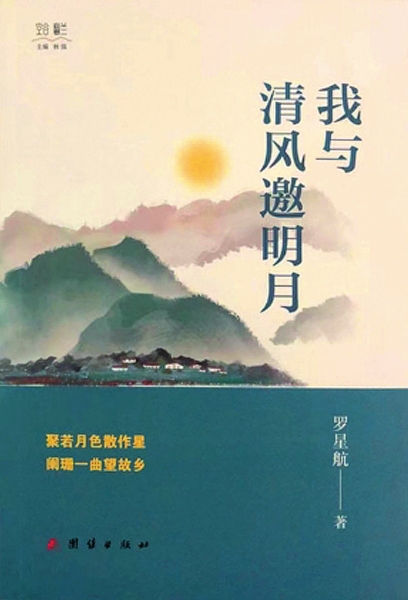|
||||
|
||||
|
□黄道培 罗星航的散文创作是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的,如同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那块邮票般大的故土。但是,却没有止步于简单对过往的复印机式的再现。正如他自己所说:“记忆的空间是有限的,只有当事情发生时,你思过、想过,并影响到你的思维和脑波,这才被储存在脑海里。时间久远,岁月流逝,一旦你被某种相似、相近的情感或物体所触动,记忆之门才再次打开,往事如水汩汩从心头流过。”(《家住文化坊》) 无疑,这种记忆是我们精神中被遗忘或者被岁月的更替所忽略的状态的复活。但他和普鲁斯特的沉重和紧张不同,他没有寻求将时光封禁或孤立,而是更致力于在构思和表达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融合与贯穿,但写作者的体验走向却是相同和相通的,“一路散步,一路饱尝风景,从沙市饭店到中商百货,共有116家店铺。”(《漫步便河》)短短一句话,便让我们以不经意的轻盈方式体验到了普鲁斯特那段写小玛德莱娜点心的刻意用心。 收录在《我与清风邀明月》中的散文,大多写的是一个城市的事,写的是一个时代的事,写的是一个人的事,这三者合而为一,交织成复调。从叙事技巧上说,还是一种细密的织体,这种细密,不刻意,浑然天成,不经意还难以觉察,仿佛自然流淌而成。然而,当我们进行文本细读时,却可以发现作者的苦心孤诣和深厚文学功底。 《记忆中的那抹暗红》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本。作者别出心裁,用红砖这一寻常可见却又常被忽视的建筑材料入手,巧妙地写城市变迁,写个人经历,写时代变化,特别是利用自己当过建筑工人的难得体验,写来别有趣味。《街头流动的风景》以自行车为主题,同样是生活中常见的物件,作者却善于寻找角度,精心裁剪,在很短的篇幅中道尽时代变迁滋味。《头头是道》写理发,我认为是作者探索此类叙事技巧最为出色的一篇。不仅现实生活的精彩折射在发型和理发之中,而且“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故事也映照出残酷的历史。特别令人叫绝的是写入了作者当知青时和大家一起将4个农村小孩当“试验品”训练理发技巧的趣事,让这一题材别开生面。看到此处时,我忽然明白过来,苦心孤诣多有,而浑然天成难有,罗星航能由苦心孤诣达成浑然天成,这不仅是裁剪功夫、编织手段,而且也体现出素材积累的巨大差异和选材的“心狠手辣”。 写老沙市,有几个题材既是必写的,也是容易被拿来比较的,就如同钢琴师必练肖邦、李斯特那几首著名的炫技练习曲以显示其功力一样。码头、堤防、洪水、内河、过早、老街、古寺、开埠、商帮、战乱、银楼、钱庄……这么多岁月堆积的往昔供我们在凝望中缅怀、辨认,时而深情时而茫然的思索中,写作者都在试图为这座多面的城市留下自己的注脚。罗星航为此用力极深。《烟雨中山路》以大雨起笔和收笔,不长的篇幅却写出了中山路的沧桑,是写中山路难得一见的佳作。《码头上的那些事儿》开合有度,收放自如,写出了沙市码头的历史变迁。《你好,早餐馆》形象生动地表现沙市过早习俗,读来趣味盎然。纵观这些佳作,体现出罗星航在散文创作上既刻意求工,又特别小心不露斧凿痕迹的匠心。我之所以认为罗星航是写沙市题材的佼佼者,首先是他在掌握丰富的素材基础上,长于剪裁,巧于安排,转接跌宕,玲珑跳脱,深得叙事逸趣,于芥子中纳须弥。其次,是他熔铸文学语言与文史考证的能力。写地方文化散文,往往有两类易现的短板,一是长于考证,短于表达,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是工于语言,疏于考证,漏洞百出,为人诟病。罗星航则做到了二者兼顾,融为一体,相辅相成。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品读其作品多遍以后才发现的。罗星航写的沙市题材,怀旧、恋旧而不守旧,尽管他未在行文中明言,但从选材和表达上可以看出,分寸感极强,迷恋骸骨的事,他是不会干的。 按照列夫·舍斯托夫的说法,作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灵感勃发地撒谎的作家(他还特意强调,要撒谎只能是灵性勃发地撒),而另一种作家则是表现自己的坦率和诚恳。罗星航无疑是属于后者,创作中注重以坦率和诚恳来表达真情实感。例如他写妈妈送别他的场景:“记得那年冬天,我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年仅17岁。走的那天,空中飘着丝丝小雨,我执意不要家人送,母亲说什么也要亲自送一程,由于转了几道车,刚到船头就已听到汽笛声,我背着背包,拎着旧皮箱,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路上母亲几次都要抢过行李都被我拦住了,这回她不知哪来的劲,一下子夺过皮箱,跟我一样从码头上沿着阶梯一步一步地往下冲。刚到船头,母亲被一块石头拌了一下,她一个踉跄栽倒在地,我急忙上前扶起母亲,只见她右手大拇指划过了一道口子,血流了出来,她全然不顾,硬是将皮箱拎到了船上,我连忙掏出白手帕,为母亲包扎好,催她快走,我发现母亲眼里溢满了泪花,不时地调转头。船渐渐离开,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只有那白手帕在江风中依然那么醒目,至今仍记忆犹新。”(《烛光里的妈妈》)真挚、朴素的感情和细腻的描写,让我们联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 罗星航的坦诚和诚恳中,还添加了一份属于他这个年代人独有的厚重。这种厚重,为特殊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所构成,上山下乡、招工回城、进厂做工、在职读书、调入机关、提拔从政……那一代人有的经历,他一样不落;那一代人难有的经历,他也深度体验。他的厚重,既有同龄人在创作选材上极其广泛的共性,也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举重若轻。后者是生活和工作中历练的结果,学是学不来的,刻意为之,只能是东施效颦。 善坦诚者,往往语言也很朴实。罗星航在散文创作中十分注重选材和结构,似乎并没有刻意经营语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精于此道,揣摩他也许是在避免以辞害意,以一种自然的文体,展现至情至性。一旦题材所需,罗星航擅写语言绮丽工练、抒情深婉细腻的美文的本领显露无疑。这本领集中体现在他的写景散文之中,如《秋醉香溪》。 捧读这本《我与清风邀明月》多遍,众多题材和高频词在我头脑中排列组合多次,逐渐形成了一个虚拟的思维导图,品味这份导图,不禁会意一笑,仿佛参透了作者创作中的一个思维秘密——刻意和随意,成了他从事散文创作中的一体两面。刻意,是每一篇散文布局谋篇、煮文烹字的认真;随意,是多年写作中有感而发、率性而作的洒脱。有些题材,一写又写,有些意象,一用再用;而且,越写越活,越用越好。特别是近年的作品,明显比早期要出色得多。写地方文化散文,确实应该是“庾信文章老更成”。从这本散文集来看,罗星航的创作正渐入佳境。更出色的作品,一定正在他的大脑中酝酿,我们期待作者下一部更精彩的散文作品早日诞生。 (罗星航,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沙市区文联主席,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罗星航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40年来,共发表散文50多万字,评论20多万字,新闻作品30多万字。著有散文集《我与清风邀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