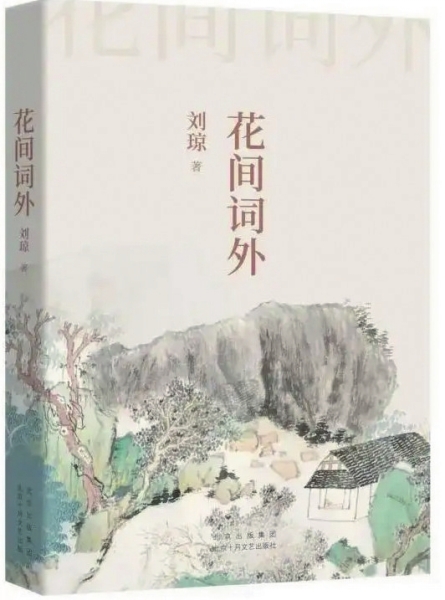|
||||
|
||||
|
读书心得 □陕声祥 《花间词外》是文艺学博士,学者、作家刘琼的散文集。初看书名,很容易想起文学史上的《花间集》,以为是其补遗、续篇之类。其实不是。《花间词外》篇篇有花,但是作者属意并不在花。她由一种花,一句诗词出发,上下勾连,天南地北,漫谈开去,引导我们去发现诗词的美、艺术的美、生活的美。读这本书,就像在茶座,听老朋友谈天。作者广闻博览,学养丰厚,侃侃而谈,妙语迭出,把读者带入艺术的境地。 古诗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因为年代久远,尘封在里面的美需要我们不断去发现,去品味。刘长卿的《采桑子》“去年岩桂花香里,著意非常。月在东厢。酒与繁华一色黄。今年杯酒流连处,银烛交光。往事难忘。待把真诚问阿郎。”据说刘长卿是皇族后裔,出身优越,却无意于功名。这首词抒写寻常物象,洗净铅华,自有一种富贵气象,有大俗,得大雅。作者对这种审美品质颇为倾心,认为非大彻大悟不能为也。读袁枚《随园诗话》,有类似的观点,“写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非精深,不能超越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解颐。”平平说来,看似浅浅淡淡,却饱含深情,受用无穷,即所谓有大俗得大雅吧。一番品读,古人词章越过千年风霜,依然熨帖人心,滋养精神。 刘琼对诗词有敏锐的艺术触觉,能独辟蹊径,多维欣赏,直击美点,融会贯通。“春在溪头荠菜花”与“春入平原荠菜花”,同为辛弃疾写荠菜花的词句。作者品出了不同况味。辛弃疾刚被罢免官职,看见溪头荠菜开花,想到荠菜已过食用期,老了,睹物伤怀,写下“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在情绪上是降调。第二年春天,看到荠菜花遍地盛开,一片繁茂,写下“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春和景明,意境开阔,明显不同于前面,是升调。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是知人论世,以生活解诗。李白和白居易,诗风各异。作者读出了他们作品相亲相近的地方。白居易的词,写得像李白的诗,豪放不羁,抒情性强,如《忆江南·风景旧曾谙》。而李白的词则写得像白居易的诗,浅白、平易、饱蘸情怀,像《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以诗解诗,又在不同诗人不同作品中,读出了共通相似处。 这本书从谈诗词出发,将诸多审美体验融为一炉,旁涉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书法,建筑,音乐等。谈到看齐白石的画展,她说,老爷子画中秋,虾和蟹都很精彩,配菊花,菊花没精打采,差了点意思。菊花被称为淡菊。画得太饱满,不像君子样;画得瘦弱,不符合实际。故而难画。真是灵想独辟,言人所未言。算是审美“科普”吧。 历数杭州名胜,自然谈到在孤山养梅花的隐士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他的名句。荡开一笔,说,比较起诗词,更喜欢林和靖的书法。除骨骼清奇之外,还有圆润、流畅和生动。不干不枯。不同于弘一法师李叔同绝了烟火气息的书法。隐士虽隐,还是活在人间。我们从中领略到书法的美,和她对烟火人间的爱。 作者谈诗论词,谈文论艺,不凌空高蹈,常常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谈,扑面一股清新之气。回忆起儿时住过的院子。“南方四季雨多,院内沿墙砌有浅浅的流水明渠,青砖压地,树荫遮日,密布的苍苔开出了细小的白花。”寥寥几句,就把儿时的生活的小院子描画出来。每天早晨,她就坐在大树下背古诗,想来,特别富有美感。 书中不仅有作者亲历的故事,更有自己的思想,频见思辨光芒。如,从辛弃疾写荠菜花,印证一个文艺学命题,“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多情是一种生理反应,在量上占优势。深情折射主体的精神气质,在深度和专注层面取胜。有无深情,是一个人的人格指标。”这是由纳兰性德的深情想到的。谈到诗教传统,感慨今天中小学诗词课“最美的东西比如音韵节奏被误读,最有价值的精神气质被忽略。”读到“鲁迅精神,是从《诗经》来,从《离骚》来,从唐诗宋词来。”心里咯噔一下,鲁迅先生不是主张读外国书,甚至干脆不读中国书的吗?忽而回过神来,《诗经》的风雅,屈原的忧愤,唐诗宋词那么多壮怀激烈的诗篇,与鲁迅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生活的美无处不在。了解我们中国的诗学、美学传统,就会懂得古人的深情,发现生活的诗意,在平淡中瞩目天地无言之大美与幽微处一缕缕的光芒,为自己建设一个情意芬芳的精神家园。诚如书中所言,知识是力量,审美知识也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