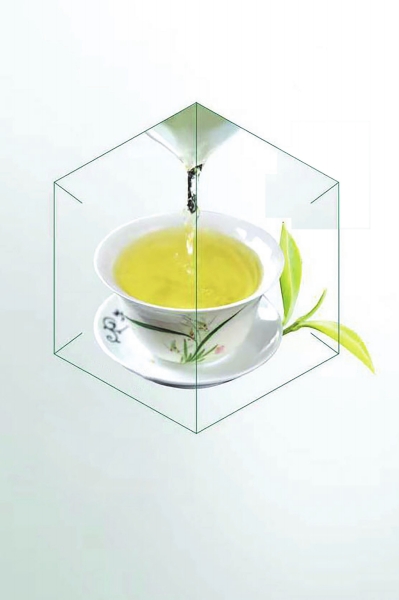|
||||
|
||||
|
□沈光明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茶文化历史的国家。当然,每个人喝茶的故事可能不尽相同,尤其是对茶的理解更是千差万别。 我最早接触茶大概是1982年春出差到成都时。那时候的成都,远没有现在的繁华与现代,倒是有点乡野味道。高楼大厦不多,街面上还有些用竹子编成的草屋之类。正是在这参差不齐、散散乱乱的大街小巷中隐藏着很多茶馆。这些茶馆有的稍显豪华,有的尽显古风,放眼望去,里面大多是竹桌竹椅,一桌人围着一把茶壶,在那里吆三喝四或窃窃私语。后来,我在读沙汀的《在其香居的茶馆里》和《淘金记》小说时,才知道四川茶风盛行,茶馆林立的原因以及吃讲茶的风俗。但这只留下了一些好奇的印象,实际上这时候我与茶没有什么接触。 真正与茶接触且进行了实地体验并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3次到外地出差。 到福建出差的那一次,真切体验了一把茶道的讲究和喝茶的程序。可能喝的是功夫茶吧,一切都很讲究。一套茶具就像工艺品,精致典雅,品质高贵;暖杯、洗茶、闻香、品茶——一套 程序下来,已经小半天的功夫,至于喝的什么茶,是乌龙,还是大红袍,我现在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而真正与茶有亲密接触是一次到杭州参观龙井茶产地及制作过程。我此行最大的收获,是看到茶农摘下茶叶后晾晒,特别在锅里揉搓制茶过程。一口大锅,加热加温后,把茶叶放到里面,然后茶农开始反复地揉搓。这个过程显得似乎有些漫长,而茶叶的香味也就在揉搓中慢慢溢出,茶叶的形状色泽也在这种揉搓中凝心聚力成为茶之上品。 但到普洱参观茶园和茶文化,感受又有不同。这个茶园很大,应该很有名气,肯定在西双版纳下面的勐海境内。但我是那种喜欢走马观花又浅尝辄止的人,现在已记不清是什么茶园了,只记得是当年茶马古道的起点。想想在古代,马帮驮着茶叶,翻山越岭、餐风露宿,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那情景该是多么苍凉与悲壮。 这些与茶有关的经历,使我在读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名篇《喝茶》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人说,周作人是最懂茶的文人,这话不假。他对茶情有独钟。在他的散文集里,直接写茶的就有四五篇,涉及到茶食、茶具、茶室、茶品等,也谈到茶的种类,喝茶的方式和用途以及中外喝茶的不同,非常全面。当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喝茶的体验。在他看来,喝茶应该是“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这实在是一种喝茶的极高境界。周作人喜欢喝绿茶,可能与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以及“半是儒家半释家”(均引自周作人五旬自寿诗)人生观有关,用清茶一杯抵十年的尘梦。可我觉得,喝茶,应根据心情、年龄、季节甚至身体状况来进行取舍。这其中的学问,博大精深。 前两天,朋友邀我到一茶室喝茶,茶室老板向我推荐了三种茶。而我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当了半天品茶师。 第一种茶是采花毛尖,我以为是明前茶,茶室老板强调是开园茶。她说,这茶,是经过了一个冬天的积累,把天地间的精华慢慢积聚,然后,一开春,嫩芽刚出,就被人采摘作茶品了。清香与清甜,娇嫩与娇羞,青翠与青葱是我对这茶的观感。这使我想起黄发垂髫,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也感受到初春的萌动与希望。喝这茶,真想哼唱王菲主唱的《匆匆那年》。 第二种是恩施藤茶。这茶,看起来如白发绾髻,丝细色白,我以为是白茶,但他们说是藤茶。喝之,入口即苦,苦到喉咙甚至肺肠;然后,慢慢回甘,当你正在失悔不该喝这一碗苦汤时,一股甘甜弄得你喜出望外——喝这茶,有一种中年人的沧桑感和苦尽甘来的感觉。 第三种茶就是熟普了。什么年份的,没有在意,但开水冲泡后,色泽红褐明亮,香味醇厚,喝之,润滑、厚重、绵密、甘甜。人说,年少不懂普洱茶,喝懂已是不惑年。的确如此。这茶,喝之,有老成持重,处变不惊的老江湖感觉。 我从不同的茶品中感受到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人生,觉得有些趣味。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既与儒释道相连,又与生命生活相通,还与环境气候水质相关,不是我所能感受到的。目前,普遍认为,喝茶比喝酒抽烟要好。人总要有点爱好,甚至有点癖好瑕疵更好。袁中郎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张岱也:“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所以,平时喝喝茶,一定可以修身养性,解除寂寞,至于能否抵十年的尘梦,那就看自己的道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