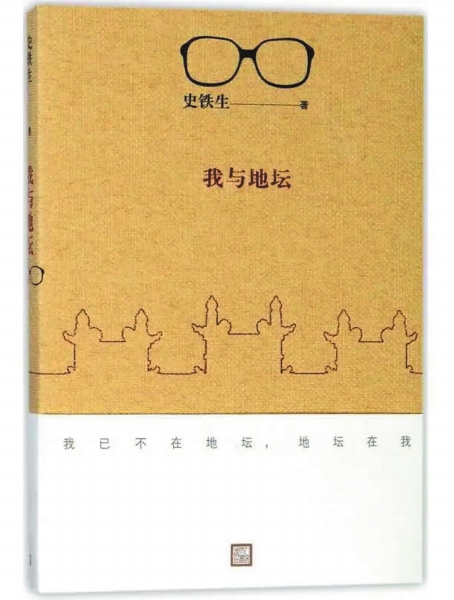|
||||
|
||||
|
□高文 初读《我与地坛》这本散文集是在中学时期,那时根本不理解书中对生命厚重感的描述。而今,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已不在人世,跨越时空,我似乎明白了他对生命意义探寻的彻底与固执,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史铁生21岁经历变故,得知余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他每一天都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对家人说:“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后来,家人不断地劝慰,还将他抬到了院子里。那一刻,他抬头看见晴天朗照、杨柳随风摆动,心里想着,失去双腿,摇着轮椅好像也不算什么。从那之后,他每天都摇着轮椅去地坛。那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废弃古园,萧瑟、破败,离他家很近。没有工作,也找不到出路的史铁生,每天都躲在废园里,静坐、呆想,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可以“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史铁生每天在地坛里消磨时光,“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这一耗,就是十五年。十五年间,他见证了地坛的变化,也遇到了很多人。还有他的母亲永远默默地跟随着。有车辙印的地方,就有母亲的脚印。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现实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也知道了,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都是加倍的。最终,史铁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后来,他专注写作,作为与命运对话的答卷。他说:“对于我而言,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文学,或不拘体裁的任何写作,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能激发生活的那种“特殊激情”,就是找到生命的意义。他写地坛里活泼的昆虫、伫立的柏树,写童年记忆里的胡同,写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他似乎真的放下了。最终,他没有被轮椅禁锢,写作让他的思想变成文字,在有限的命运中,走出一条无限善美的路。 生命的意义很难定义和描绘,只有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刻体会生的意义。残酷的命运击败不了他,活着,就好好地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