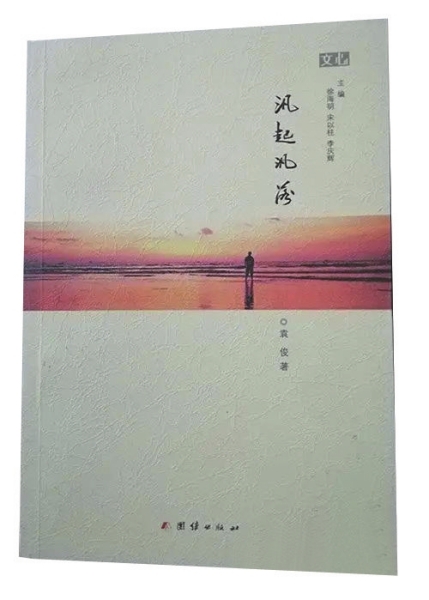|
||||
|
||||
|
□罗胸怀 麦家说:“我对故乡有一种警惕、怀疑,甚至有那么一点敌意,但一辈子总要写一部跟故乡有关的书,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我不知道袁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文写作,但读罢他的散文集《汛起汛落》,我知道他的散文写作一定与故乡有关。 每个人对故乡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归纳来说,大体是这两种情况,一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总想走出故乡,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去领略、探寻与故乡不一样风景和人生际遇;二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时,总是想回到和亲近故乡,让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沐浴自己满是人世尘埃的灵魂。因为故乡的明月总适合入怀,因为故乡山水总是远近相安,因为故乡的烟雨中总能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可能正因为这些,可能是一种宿命,故乡的人和事,山川草木,遗址风物,是每一个写作者都绕不开的写作对象,这一切也在袁俊的散文作品中出现,且娓娓道来,是那么从容和不惊。譬如,他的《赤壁怀古》《沉思在历史的桥头》《古战场的黄昏》《石林风光》等等。这一类题材,一些散文作者或者说是散文作品,常常会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自己的“坑”中,轻车熟路地把所见所闻写得非常精美,反倒是让这些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和思想力,除了“一层皮”似地描写,没有了血肉和筋骨。 纵观袁俊的散文作品,他不是简单的写景状物、吟月颂风、抒发小我,也不是埋头故纸堆里对历史进行复述,他善于把这两者进行结合,把自己溶入在字里行间,去领悟,去抒发,去享受。正如他在《赤壁怀古》中所写:“任凭心灵去感受,遐想在月亮中在月光里,人与月相交融,伫立在江风习习的赤壁崖前,仿佛超越了历史空中,一种永恒的精神浸润着我的心灵。”他这样的书写,在他散文创作经验中的蓄谋已久还是突发奇想,我不想去探究,我要说的是,这种语境很容易让我想起苏轼的《赤壁赋》,赋中以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体进行形象注解,在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其赋空灵并富诗意。从地理概念而言,他们笔下的赤壁不是同一个赤壁,但从文学概念而,袁俊在周郎赤壁的感发,与苏轼《赤壁赋》的语境有一种不约而同之妙。 如果说袁俊散文作品中的虚笔,是对历史进行一番打量和思考后的追记,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则是在写实的笔端,浓墨重彩地对故乡这块土地上人间亲情进行温暖的感知。如《父亲是木匠》中父亲以一个木匠对木器的担当对他人生的影响,如《清明祭兄》中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和对曾经的回忆,如《倚在门槛边的凝望》中记述门槛旁不再的母亲凝望的眼神,如《驻村的日子》中一个个善良而勤劳帮扶对象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还有《汛起汛落》《童年暑事》等等。这些平凡而又对他来说相当重要的事和人,构成了他人生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在他看似拙朴的写作和文字中,让人感到一片真情扑面而来。 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且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以写人写事为衣钵,把人生的情感体验进行意境深邃的表达,在我看来,袁俊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做到了,而且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给人以温暖。 或许我无法对袁俊的散文写作进行一个精准地评判,但他能写到这个分上已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