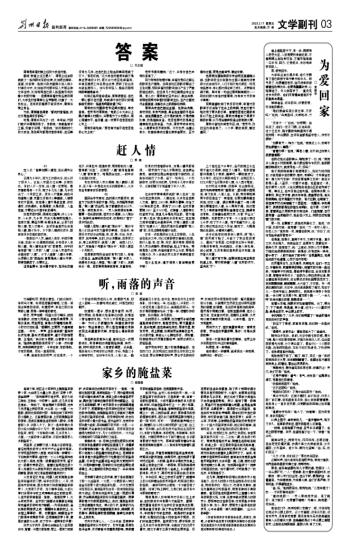|
||||
|
□杨朝贵 每到冬季,城区各个菜市场上腌制盐菜的萝卜菜、大白菜又大量上市,路边“卖萝卜啰、卖白菜啰……”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前不久还二块钱、三块钱一斤的萝卜、白菜,这几天只有五角钱、一块钱了。可能是暖冬的原因,过去冬天很难上市的芥菜、大头菜,也一大捆、一大捆的,被附近卖菜的村民一车车拉到了菜市场的小摊贩上。这些青翠欲滴、上好的腌制盐菜的原料,在讲究健康生活的城市人眼中,只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了。除了一些年龄稍大点的大妈大婶偶尔买个几斤一把,临时腌点新鲜的盐菜,满足一下怀旧的口感,几乎没有人一大捆、一大篮的像从前那样,买回去腌制那么多的盐菜了。 而盐菜,这种眼下被人有些淡忘的菜品,曾经却是我的家乡家家户户必备的家常菜。对于现在的城市人而言,或许只是一种调剂一下口味的开胃菜,但对我一个从小吃盐菜拌饭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一段最难忘的岁月,留下过一段最珍贵的记忆。看着这些现在已很少有人问津的大头菜和芥菜时,就会让我想起那段醇香、酸甜,却又有些苦辣的童年时代! 从我有记忆开始,村里人就有腌制各种盐菜和酱菜的习惯,每年农历的七、八月,村里每家的菜园,都会栽种大块的腌制盐菜的萝卜、大兜菜及芥菜。当冬春季来临,大伯大婶们会用中午收工或早晚未出工时的空闲,从自家的菜园背回一背篓、一背篓的萝卜、大头菜或芥菜。各家的门前都会将腌制各种盐菜或酱菜的菜叶进行晾晒,一片绿油油的,连低矮的厨房顶上或一棚棚未长高的树上,也会挂上厚厚的一层。放眼望去,晾晒在各家门前绿中透黄的芥菜、红绿相间的萝卜菜、青翠欲滴的大头菜,成了村子一道特有的风景! 我家也不例外,母亲也会抽出几个空闲的日子,背着一只偌大的背篓,带上一把菜刀或铁铲,去菜园将已成熟的芥菜砍下,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回家里,简单地择捡一下,用竹篮提到堤外的水塘边清洗干净,待菜上的水珠滴落沥干后,再放在门前早已摆好的胶布或晒垫上。经过几日的晾晒,萝卜或芥菜的水分被晾晒得差不多干了,那肥厚宽大的芥菜叶已变成了皱巴巴的深绿颜色,而腌制盐菜的工序就到了最费工夫的切盐菜的时候。按母亲的吩咐,我会找来家中那个最大的木盆,在木盆底下,放进家中那块最大砧板,再将晾晒干的芥菜一小把、一小把理顺,然后拿到母亲的面前。那芥菜在母亲磨得光亮的菜刀下,几个小时的功夫,一大木盆切得粗细均匀的盐菜便切了出来。 稍稍休息一会,母亲让我帮她把因长时间切菜而有些僵硬的手臂轻轻揉捏几下,待僵硬的手臂稍稍缓解一些,便让我将从厨屋端出的那个瓷碗大小的盐罐放到她的手上,母亲随手将有点粗大的盐颗粒均匀地撒在切好的盐菜盆里,双手在木盆里将盐与盐菜反复搅拌均匀,只是拌着拌着,母亲的双手已被盐颗粒浸得通红,手上粗糙的皮肤已透出了一条条细细的血丝。 母亲顾不得手上的疼痛,接下来将揉腌好了的一大盆盐菜,一大把、一大把的装入早已准备好的那个很大的盐菜坛里,一次次反复用手压紧压实,直到盐菜坛内有一股深绿色的盐菜水滤出,母亲会将盐菜坛上盖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装满盐菜的坛子倒铺在铺满一层厚厚的草木灰的厨屋的地上,此时,腌制盐菜的工序总算基本完成。寒冷的冬夜,昏黄的灯光下,深夜的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伸伸腰,扬扬脖子,再用胳膊肘揉揉眼睛,简单地洗漱完毕,上床休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二十天后,母亲亲手腌制的盐菜可以开坛吃了。打开坛盖,那满坛色泽金黄,浓浓醇香中透着微微酸味,裹挟着芥菜味道盐菜香味,在满屋飘散开来。 此刻开始,全村人也会和我家一样,一日三餐盐菜下饭的日子,又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轮回起来。少许家里条件稍好点儿的伯伯、叔叔,还能在盐菜中打上一个、两个鸡蛋,看着那金灿灿、黄澄澄、香喷喷的盐菜炒鸡蛋,喝上个一两、二两的白酒,此时,那种酒足饭饱的惬意和满足,在队长门前那棵歪脖子槐树上的一阵“叮咚、叮咚……”的破铁犁声响过之后,随着队长从村头到村尾的“出工啦、出工啦!”的叫喊,全队的社员开始走出各自的家门,有的下地耕田,有的耙地,有的锄草,有的栽苗。村里的男男女女下田干着农活,似乎都有股使不完的力气。那咸菜如同有着山珍海味般的美味和营养,人人有说有笑地挣着队里的工分。 说实话,尽管母亲腌制的盐菜金黄透亮,吃起来也酸爽脆香,非常好吃,但我却很不喜欢吃这盐菜。小时候,盐菜似乎是我家饭桌上每餐必有的主打菜,一年四季,那张陈旧得表面油黑、且有点破败的八仙桌上,似乎都是它的身影,吃多了,再好吃的东西也就没有味了。中午还好,早上上学或干活累了,就着早上的冷饭拌着金色的芥菜盐菜,吃起来还是比较香的,一碗菜风转残云般地一下子就吞进了肚里。可到了晚上再吃,又是它时,就没有中午那样的感觉了! 特别是进入初中离开村子到公社上学后,住校的日子只有周六才能回家。星期一把家里背来的米交给学校的食堂换成饭票,菜是食堂没有的,除了专给老师做点吃的菜外,平时是不对学生卖的。就是学校食堂有菜卖,也是我们这些乡村学生买不起的。我们只能自己带菜。盐菜因下饭、便于保存,放上几天也不会变质坏掉,也就成了我们很不喜欢,却又不得不三餐不离的主要菜品。好在那时生活条件都差,除了极个别同学偶尔带来点自家摸的虾子、小鱼外,能带其他菜品的同学几乎没有。而这也成了同学之间谁也不会笑话谁的默契。所以,每到了周一的早上,那些叮叮当当响的罐头瓶里,全是些金黄的芥菜、乌黑的萝卜、翠绿的大头菜盐菜。每当学校开饭的铃声响起,同学们打开自己的菜瓶,学校的食堂门前,摆放的萝卜、白菜、大头菜、芥菜等,各种颜色的盐菜就好像是在开办一个盛大的盐菜宴似的,而这样的画面,直到现在,也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最深处! 后来,我进城工作,虽然工资很低,食堂那盐菜虽然只卖一分、二分钱一碟,我也很少吃它。特别是结婚成家后,随着生活的越来越好,饭桌上的一日三餐的菜品也越来越丰富,鸡鸭鱼肉对家里来说早已是平常之菜。而盐菜对我来说也就基本上再没吃它了。后来,有时妻子在菜市场买菜时,看到油光发亮的金黄色芥菜盐菜时,也会买回一碗、二碗,而我也总是对她嗤之以鼻,说:“你别再买盐菜了!”而妻子则回怼我说:“你不喜欢吃,不吃就是了!”我无法,只有随她好了。 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离开家乡越来越久,我对儿时的乡村生活却有点怀念起来,特别是伴我一起长大,吃得有点腻味、曾经发誓再也不吃的盐菜,更是有种说不清的情感。看见那些在城里菜市场上推着小车大车卖菜的大妈、大婶,无意中就会想起儿时的家乡,想起早已过世的母亲,还有那些多年未见的乡亲、发小、同学,想起家乡盐菜泡饭的岁月,心中会涌起一种久别的温暖,一丝淡淡的辛酸! (作者系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其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于《雨露风》《精短小说》《参花》《速读》《今古传奇》《新浪潮老朋友》《荆州日报》《鄂州周刊》等报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