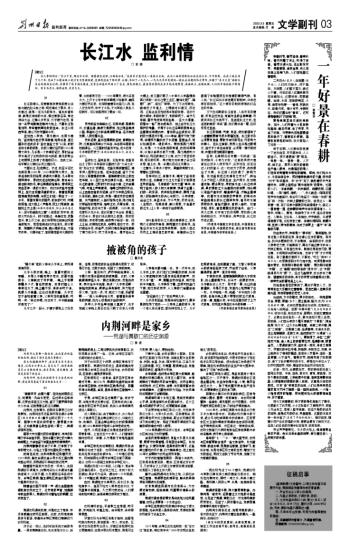|
||||
|
□曾繁华 早春时节,春雨连绵,春寒料峭。春风吹醒了冻土,吹绿了田园。春雨滋润大地,泥土散发芬芳。麦苗青翠,油菜金黄,鸟儿在田园上轻舞飞扬,人们在地里忙着春耕。 二月初头(农历),白田里(指旱地),人们挖沟排水,待干整田。水田里,人们暂不蓄水,就这么干着。只见庄稼人扛着铁锹走在田间地头,这里转转,那里瞄瞄。白田、水田,在田的豌豆、小麦、油菜作物等一一看遍,挖缺放水,疏通沟涧。细小末节、手脚到位。我们这里俗称“看田”。这可谓是春耕时“打前哨”吧。 要是早黄豆田还得趁早耕作。如今,人们开着大小机械耕地整田,请来师傅,免了劳累,节省了时间。只要事先在地里撒播肥料就行了,春耕轻松便捷。望着机械耕整的田块,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单干初期,人们种田的激情一下迸发出来,家家都种田,人人都出力。恨不得把田“摞”起来。一季接一季,一茬接一茬。人不闲,田不空。那热火朝天的春耕生产催人跟进。我最难忘的是人们在田间赶着耕牛耕地的情境。照说,我们地处水乡,水田白田各半。那时春耕就靠牛的力量,按牛的“份子”轮流整田。牛“份子”来了,就趁着好天气抢晴动手。田野上呈现出“耕牛遍地走”的景象。忙碌的人们,一手拿麻鞭,一手扶犁拐。麻鞭扬起,口里吆喝。一阵“嗐叽、嗐叽……”,牛儿就在一阵阵的驱赶声中负重前行,身后均匀地留下一块挨一块的“犁垡”和一行挨一行向上翻着的土块。就是这么一犁接着一犁,在不经意中翻耕的地面慢慢扩大;就这么一圈接着一圈,在麻鞭的响声中田块慢慢缩小。人赶牛,牛随人。耕完一块田走了多少步,谁也没有数过。人赶牛,又怜牛。人牛相依,步步向前。纵使累得疲惫不堪,也无怨言之感。田间吆喝阵阵,麻鞭水响,庄稼人劳作的模样,绘成了田野上一道万“牛”奔腾的风景。 我出身农家,种田是个“横手板”。耕田整地,我有过胆小紧张的无奈,有过得心应手的喜悦。刚开始,我只会耙田打滚,不会耕田。后来的日子,我的父亲年迈力衰,不能耕田了,再也不能让妻子去与人家换工耕田,只有自己动手。耕田还是有技巧的,要划算。不规则的田拐弯抹角。怎样下“埸”才不走冤枉路。除了掌握好犁拐子,不跑边,“吃土”适中(不深不浅),还要耕得厢子均匀而平整。可谓是耕田的基本要求。按原厢子耕就是“蓬厢”。要改厢子就耕“开厢”。这“蓬厢”就按原来的“埸行沟”,这“开厢”就得另外开“埸”了。经过几番摸索,我也学会了耕田。望着耕好的田块,身子的劳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种劳动后的喜悦涌上心头。 我能自由自在的耕田了,再也不用求人了。我常常抢住大好晴天忙着春耕。把自己融入在美好的春光里,走进那春耕的茫茫人流中。 俗话说,女子的鞋边,男子的田边。一块地翻耕好后,要耙、要磨(磨平),把土整细,拖沟、扒沟(水田还要耖田)等。这田边要整得成方成块,边角到位。以免旁人说闲话。在那“半耕半教”(民办老师教书种地)的日子里,每当放学后、星期天,我就忙着整田了。这耕白田还轻松一点,耕水田却不那么容易。那时候,人们在头年的冬腊月间就打“冬耕板”,随后就是“关冬水”,让冬水长期泡着。到第二年开春,再过“二到犁”。这耕第二遍,恰遇春寒,水凉冰冰的,泥土黏糊糊的,泥脚又深,当时被称为“冷浸田”(这样的田插早稻容易“坐蔸”)。要转埸了,手拉“二拐”拖动木犁,连人身上的筋都要拉动,胳膊酸痛,眼冒金花。人累得筋疲力尽,但休息一两天,身体又复原了。尽管我的手拉牛绳、扶犁拐,手板发红、发痛,手上就像长了细细的锯齿,生怕与人家握手,但我一直坚持着,从不泄气。春耕时节,田间布遍了我的脚印,洒下了我辛勤劳作的汗水。便是如今年纪大了,仍然吃苦耐劳,纯朴、勤奋的本色依然没有改变。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种田的庄稼人都用农家肥。牛粪、猪粪、草木灰、青草、青苗等。打好冬耕板的田里,父亲就把牛栏铺、猪窝草等撒到田里,以便春耕时把肥料耕入田间。这算是水田的底肥吧。还有“告”早黄豆的白田,人们也是早早把沤着的草木灰拌了磷肥一担一担挑往田间,一小堆一小堆有顺序的堆着。那送肥到地头的情景相逢招呼、好不惬意。 而今又到春耕时,所不同的是机械取代了耕牛,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小小三轮取代了肩挑步行,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坚守田园。已经不是那时成片的田块,而是成片的虾池、养鱼植莲。这里的水田只种一季中稻了(没有了早稻和晚稻)。相对而言,随着乡村产业化的蓬勃兴起,春耕备耕有了新的方式,但在人们各自的打算中忙而有序,悠闲有度。 布谷声声春耕忙。水乡的大地上,遍涌春耕备耕的热潮。色彩日渐丰富的田野,寄托着庄稼人一年美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