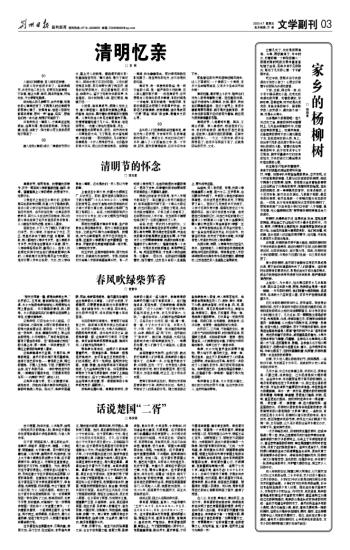|
||||
|
□曾繁华 “楚天云雨第一雷,便是柴笋破土声。”农历的二、三月间,春日暖阳加上春雨滋润,水乡大地的柴笋悄悄地从河堤荒地池埂上冒出来,一片齐刷刷的青绿,袭人眼球。水乡的婆婆妈妈们拎着布袋在田野上寻觅,忙着采摘柴笋。 这柴笋呀,它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它不择地域,不择环境,只要它的根伸到有土的地方就能冒出来,根的每一个节巴上冒出一根柴笋。鱼池、藕塘的田埂上,墩台前后的坡地、小沟河堤边、厂房的角落地面,都有它冒出的身影。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浅草丛中,那一窝窝、一块块青色的、下褐红上青绿的柴笋惹人喜爱。 这柴笋美得并不空洞。它是干柴、芦苇的嫩茎。虽然它的长相不是花里胡哨,但有它自己的本色——青绿的上装,褐红的裙摆。不需人工栽培、下肥,不需要打药治虫,无丁点的污染。一种朴素而自然的美,一种藏而不露的本性。它把最有用的东西——内藏的“笋芯”,献给人们。 这柴笋采摘方便。老人们戴着手套,就地取材。选取两手掌多高的柴笋掐除上面的叶稍装入布袋。阳光下,柴笋苍翠耀眼;雨后,柴笋翠绿明亮。春风里夹杂着刚出土柴笋的淡淡清香。人们不分时段、不顾晴雨,只要愿意就奔向近处的田野村落。她们肩背手拎,大小兼容,四处寻觅。近处的步行回家,远处的就开着小车运回来。 采回的柴笋还得焯水。青青的不能直接上市。蔬菜焯水那是家庭主妇的拿手戏。农家的大锅柴火灶,木柴火烧得旺旺,锅里的柴笋满满。待水烧开滚烫之后,就把柴笋翻一翻,让柴笋均匀煮好,不见青色。煮好后的柴笋迅即捞到盆里,稍待片刻,人们就开始剥柴笋了。 剥柴笋也有讲究。出锅不久的柴笋冒着热气,一股清香扑鼻。剥柴笋一般是在夜晚进行。左邻右舍三三两两的老人们过来帮忙,洒下一地闲话,呈现两手忙碌。说着、剥着,当手指甲间染下黑色的斑迹,几大盆柴笋已剥下来。只见根根柴笋剥去了外面几层的粗叶,去掉了上面掐不动的部分,留下了黄白嫩生的笋芯。一盆盆用清水浸泡着,那一根根鹅黄的小柴笋明亮亮的,耀眼惹人。 卖柴笋无需吆喝。清晨的菜市场,卖柴笋的小摊点一溜儿摆开。新鲜嫩黄的柴笋吸引着川流不息的买菜人。他们指指点点、前来光顾。“这柴笋新鲜,昨晚剥出来的。”“这个么价呢?”“还不是大行市,前些天卖过上十块,近几天卖到六、七块。”一番讨价还价,人们就开始选择柴笋了。这些买主十分讲究,捏一捏、闻一闻、看一看,少了水分才买下来。多则大几斤,少则一两斤。那第一批采摘的柴笋粗壮、白净、颜色好,留“尾”不长。自然就成了“抢手货”。就这样,老婆婆、大妈们各自的或多或少的柴笋就卖光了。一早晨的光景,老人们挣了几个油盐钱,心里自然舒坦。 后来随着天气转热,出远门的、就近的打柴笋的人们多起来,卖柴笋的小摊也增多了。这柴笋一多,价格自然就会下跌,只卖四、五元一斤了。农家老妇人的柴笋有时卖不完,剩下的就带回家,把它压干脱水,放在冰箱里,吃上三、五个月也没问题。 青黄不接柴笋正当时。那时农家菜园里青菜蕻子下架,莴笋还未长成。柴笋上市弥补了人们餐桌的不足。随之而来的这些柴笋就进入餐馆,进入寻常百姓家。柴笋的食用真是五花八门:凉拌、清炒、炖煮、下火锅、做熟食皆可,亦可与鱼、肉、鸡、蛋配制成菜。常见的是柴笋炒肉丝,清香绕盘,味美可口。据说,它和蒲菜、茭白一样,是非常不错的野味。它还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既饱口福,也利健康。就地取材,经济实惠。可谓是一碗难得的时令美菜。 农历的二、三月间,万物蓬勃生长。春上的天气时而艳阳普照,时而春雨连绵,既温暖又湿润。采掰后的柴笋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人们间歇性地采摘,不断地为市场输送鲜货。柴笋又成了一碗抢手菜。 柴笋,水乡大地自然生长的野外植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复一年,繁衍生息。出土不久的柴笋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野味,待后来长成干柴,身材好一点的成了人们编扎的材料,其它的可用来做柴烧。柴笋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的奉献人类,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德?难道不是大地的恩赐? 柴笋飘香上餐桌,水乡老妪采摘忙。她们时不时地去野外采摘,给自家挣点收入,给市场输送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