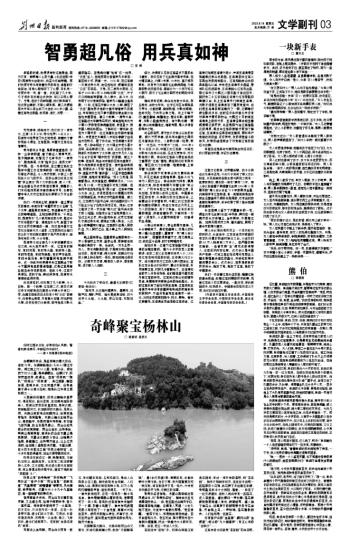|
||||
|
□ 安频 年轻的时候,我便很爱听红色歌曲,因为它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长征组歌》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我至今还能哼唱。那时我便对赤水河有着天然的向往,虽暂时不能前往,可是心里却存下了心愿,有机缘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忙碌了几十年,终于退休有时间出去转转,可以实现心愿了。于是,在初冬的暖阳里,我们乘车南下,抵达茅台镇时,不禁心潮澎湃。第二天便和朋友开车从茅台到习水往返400多公里,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我观察、追忆、沉思…… 一 走走停停,逶迤而行,我们去了一渡赤水、三渡(在茅台镇)赤水地界(二渡没去),四渡赤水地界在习水土城老街,接着去了青秆坡战斗遗址、红军医院、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等处。 贵州的天分外蓝,是那种宝蓝色的、不掺一丝杂质的蓝,看了就让人神清气爽。草木掩映间,我瞥见了毛体书法“一渡赤水”,飘逸挥洒,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在一处楼观前,竖立着红军战士擎举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一排红色浮雕,场景庄严神圣,令人肃然起敬,不禁让人想起战火纷飞的岁月。在茅台渡口还竖立刻着“茅台渡口”四个大字的长碑,高11.7米,碑名由著名书法家陈恒安题写,提醒的人们永远铭刻那段传奇的革命岁月,也寄托着中华儿女对红军的无比崇敬以及怀念的深情。 我们一行来到土城,前面有一座上覆石瓦的牌坊,中间刻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几个大字,道路刷成迎宾红,象征革命烈士走过的峥嵘道路。土城古镇很繁华,“千年土城、四渡赤水”几个铁片拼成的大字,胜过千万句华丽的广告。建筑古朴大气,彰显了传统文化历史辉煌的一面。我还在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前与友人留影,红军医院纪念馆门前台阶下两边摆放着的不是严肃的狮子,而是可爱的小象,十分有趣。 四渡赤水纪念园几个大字被镶嵌在大石之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红军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有时声东击西、有时杀回马枪,牵引着国民党军疲于奔命。这一作战方针使得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是红军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胜利。在战斗中,红军不畏艰险、百折不挠,铸成民族魂,四渡赤水精神将彪炳史册。 我在游览时,还收集了几个故事,令人回味。第一个故事:红军第二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都是在古蔺县太平镇太平渡口一带,古蔺东南部的回龙场有个叫“云庄”的寨子,内有亭台楼阁,外有高大石墙,环绕护庄水壕,还安放两门大铁炮,扼守当年川黔大道的隘口。正是倚仗着“地利”这一优势,“云庄”主人、当地民团长官曾庶凡多年来一直压榨乡邻、祸害一方。1935年,在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途经当地时,便遭到来自“云庄”的袭击。于是,在二渡赤水期间,红军于1935年2月15日晚包围“云庄”,并于次日傍晚越壕翻墙,攻入寨中。战斗中,反动团丁纷纷缴械投降,曾庶凡从暗道仓皇逃跑。17日,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镇压了“云庄”里作恶多端的大管家等曾庶凡的帮凶,并将相关土地及寨子里的钱粮全部分给当地贫苦百姓。第二个故事:一渡赤水后,红军路过太平镇走马坝时,适逢当地贫农方少周69岁的老母亲病重在床,危在旦夕,而家里人却无钱医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住在方少周家的一位红军营长主动前去看望病人,并把自己珍藏的人参无私奉献了出来给方母熬汤。服了参汤后,方母病情大有好转。老人的命保住了,方少周全家老小喜不自禁,连连感谢红军。后来,这位红军营长随部队开拔离开了太平镇,但方家几代人始终念念不忘其“赠参救母”的恩情。第三个故事:在军阀、地主与奸商的压榨与盘剥下,赤水河两岸的贫苦老百姓一度吃盐非常困难,即便许多人干起“背盐工”,每天辛苦劳作,但盐依然是“奢侈品”。以至于在古蔺县二郎镇,当地还有首民谣:“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1935年2月18日,一支红军部队攻克二郎镇。在军阀开在当地的盐号“四公益”,红军举行群众大会,会上,贫困老百姓纷纷揭露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并表达对吃盐的渴望。第二天,红军便打开盐号仓库,将奸商囤积的6万斤盐全分给了当地贫困老百姓。随后,红军又截获了另一家奸商“集大成”盐号尚未卸下的12船盐,也陆续分给了当地劳苦大众。经过三天三夜,待分盐完毕后,这支红军部队才渡过赤水河,跟随主力再入黔北。从这些小故事里可以看出,红军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为人民打江山,在小事上为人民排忧解困。 晚上回到茅台,在国酒茅台集团旁边一家小餐馆吃土家菜、品茅台酒,那种感受和味道还真的不一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赤水河酿造的酒,不是别处可以酿造出来的。西南风情,得天独厚,在群山环绕的小镇上快乐地吃一餐饭,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这里家家卖酒,喝酒的人很多,酒香飘散,酒不醉人人自醉。 二 今天我去了娄山关,重温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读之,仿佛可以见到红军坚贞不屈的战斗情形。我还见到了毛主席行草手书体,在大理石碑上,约莫3米高、10米长,呈不规则菱形。还有专门修建的毛主席诗词馆,为典型的黔北民居风格,里面分为一个序厅和五个展厅,展示了毛主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诗词成就。 相关资料记载,娄山关亦称太平关,原名娄关,后称太平关。位于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古称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上千峰万仞,重峦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作为黔北第一要塞,娄山关峭壁绝立,雄奇秀丽,是众多游客的常去之地。 关名的来历,源于古代对娄山山脉的称谓。明代万历年间,总兵刘与播州土司杨应龙曾激战于此。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1935年2月25日至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黔军大战娄山关前,经过反复争夺,歼灭黔军两个团。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后来成了重要的“红色”基地,遗址附近还有陈列馆。景区的大门口砌着一堵青砖墙,上面写着“长征第一捷”。 娄山关脚下还有娄山关大捷实战演习,只见红军战士英雄伟岸,在战火纷飞中为人民打江山。娄山关桥为拱形,横跨两山之间,桥栏中间朝外刻着毛体“娄山关”。广场中央竖立有毛主席的立像,目光如炬,好像刚从战场上归来。中国革命老区的板标,纵深裂纹的仿红色山石,上面露出右手扶着枪柄,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绕着枪柄飘扬,象征红军在这片热土上为人民的解放,洒下了鲜血。还有好似羽翼的模型,底部卷着枪柄,下面刻有一句话“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向胜利”。我看得热血沸腾。 从娄山关到遵义,茅台的朋友驾车,几十分钟就到了。最初知道遵义,还是儿时听别人唱《长征组歌》,里面有一句“遵义会议放光辉”。因着歌词豪情万丈,而又朗朗上口,故我至今记得,时不时哼唱两句。 当地还有一位曾为红军指路村民王海清的后辈王善明。据六十多岁的老人王善明讲,他的二伯父王海清姊妹共八个,1935年红军来到村里的时候,王海清大约三十岁。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大肆污蔑言论,宣扬红军会抢占村民财产,霸占村民房屋,极尽抹黑红军,村民几乎都跑光了。王海清和他的家人没有逃走躲,他们躲在屋子里观察外面红军的举动。红军到达娄山关时情势紧迫,急需制定突破娄山关的作战路线。此时红军找到了当地村民王海清,红军来到王海清家中并没有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抢夺村民财产,不但没有拿走王海清家一针一线,反而主动帮其扫院子、挑水、劈柴。看到这种情况,王海清主动出来和红军讲话。红 军亲切地喊王海清为老乡,并问王海清是否知道通过娄山关的路,王海清告诉红军从东西出发的两种路线。红军知晓娄山关的具体路线以后,并未在王海清家多逗留,带领队伍迅速前进,王海清担心红军走岔路,带红军走了大概五公里的路才独自回家。国民党二十五军知晓王海清为红军带路的事情以后,找上王海清家门质问王海清。沉默不语的王海清激怒了国民党官兵,他们把王海清吊起来毒打了一顿,这顿毒打使他卧床多日,当时经济条件差也并没有对其进行更好的救治,大概三个月时间王海清身上的伤才好。王海清经常会和王善明提起这段历史,也正是因为给红军指路这段渊源,通过与红军的接触才更加了解红军,王海清也经常告诫王善明,要听共产党和政府的话,好好劳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朴素的话语饱含了对党和红军的信任与依赖。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回来的,我们要倍加珍惜,牢记长征精神。 三 红色文化教育,滋养着后辈。我十分向往这处革命圣地,今天终于来到了遵义会议旧址,只见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的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旧址檐下悬挂着毛主席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6个字的黑漆金匾,内面保存有红军标语,有一间铺面房是当年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用的,还有当时的桌椅板凳等物件,似乎还原了那个色彩斑斓的激情年代。 长征在遵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遗址内有毛主席《长征》手书体,镌刻在一面巍然的长方体墙上,金字黑底、外围赭红色。如携风雨凌厉之势,铺天盖地,展现了革命家的博大情怀。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长征途中,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曾支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我们一行沿着红军长征的路,唱着红色的革命歌曲,收集红军时期的历史故事,观看红军战斗的实景演出。一路行来,使我感悟很多,收获很多。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