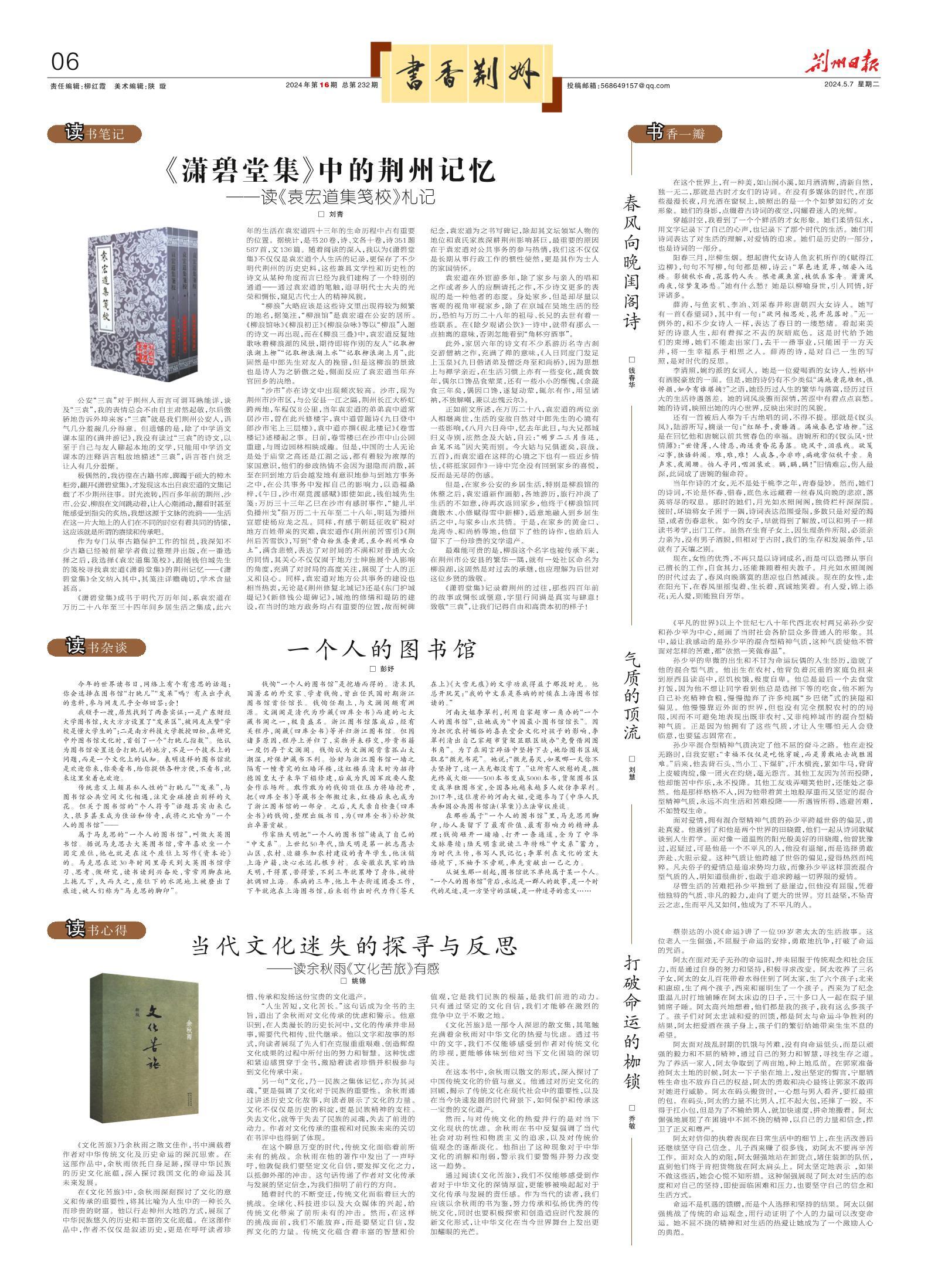□ 彭妤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网络上有个有意思的话题:你会选择在图书馆“打盹儿”“发呆”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参与网友几乎全部回答:会!
我顺手一搜,居然找到了两条实证:一是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大大方方设置了“发呆区”,被网友点赞“学校是懂大学生的”;二是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田松,在研究中外图书馆文化时,首创了一个“打盹儿指数”。他认为图书馆安置适合打盹儿的地方,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上的认知。表明这样的图书馆就是欢迎你来,你要看书,给你提供各种方便,不看书,就来这里坐着也欢迎。
传统意义上颇具私人性的“打盹儿”“发呆”,与图书馆公共空间文化相遇,注定会碰撞出别样的火花。但关于图书馆的“个人符号”话题其实由来已久,很多甚至成为佳话和传奇,我将之比喻为“一个人的图书馆”——
属于马克思的“一个人的图书馆”,叫做大英图书馆。据说马克思去大英图书馆,常年喜欢坐一个固定座位,他也就是在这个座位上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在近30年时间里每天到大英图书馆学习、思考、做研究,读书读到兴奋处,常常用脚在地上拖几下,久而久之,座位下的水泥地上被磨出了痕迹,被人们称为“马克思的脚印”。
钱恂“一个人的图书馆”是挖墙而得的。清末民国著名的外交家、学者钱恂,曾出任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任期上,与文澜阁颇有渊源。文澜阁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极负盛名。浙江图书馆落成后,经有关程序,阁藏《四库全书》等并归浙江图书馆。但因诸多原因,程序上并归了,实物并未移交,珍贵书籍一度仍存于文澜阁。钱恂认为文澜阁背靠孤山太潮湿,对保护藏书不利。恰好与浙江图书馆一墙之隔有一幢考究的红墙洋楼,这红楼系清末时为招待德国皇太子来华下榻修建,后成为民国军政要人聚会作乐场所。敢作敢为的钱恂顶住压力将墙挖开,把《四库全书》等藏书全部搬过来,红楼后来也成为了浙江图书馆的一部分。之后,天天亲自检查《四库全书》的钱恂,整理出版书目,为《四库全书》补抄做出卓著贡献。
作家陆天明把“一个人的图书馆”读成了自己的“中文系”。上世纪50年代,陆天明是第一批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建设的青年学生,他注销上海户籍,决心永远扎根乡村。在安徽农民家的陆天明,干得累,苦得紧,不到三年就累垮了身体,被特批调回上海。养病的三年,他上午去街道团委工作,下午就泡在上海图书馆,后来创作出时代力作《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的文学功底得益于那段时光。他总开玩笑:“我的中文系是养病的时候在上海图书馆读的。”
河南大姐李翠利,利用自家超市一角办的“一个人的图书馆”,让她成为“中国最小图书馆馆长”。因为担忧农村媚俗的喜丧堂会文化对孩子的影响,李翠利清出自己家超市货架显眼区域办“免费借阅图书角”。为了在闲言碎语中坚持下去,她给图书区域取名“微光书苑”。她说:“微光易灭,如果哪一天你不去坚持了,这一点光都没有了。”让所有人欣慰的是,微光终成火炬——500本书变成5000本书,货架图书区变成单独图书室,全国各地越来越多人效仿李翠利。2017年,这位质朴的河南大姐,受邀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立法审议座谈。
在那些属于“一个人的图书馆”里,马克思用脚印,给人类留下了最有价值、最有影响力的精神真理;钱恂砸开一堵墙、打开一条通道,全为了中华文脉赓续;陆天明靠就读三年特殊“中文系”蓄力,为时代立传,书写人民记忆;李翠利在文化的宏大语境下,不袖手不旁观,率先贡献出一己之力。
从诞生那一刻起,图书馆就不单纯属于某一个人。“一个人的图书馆”背后,永远是一群人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是一方坚守的温暖,是一种追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