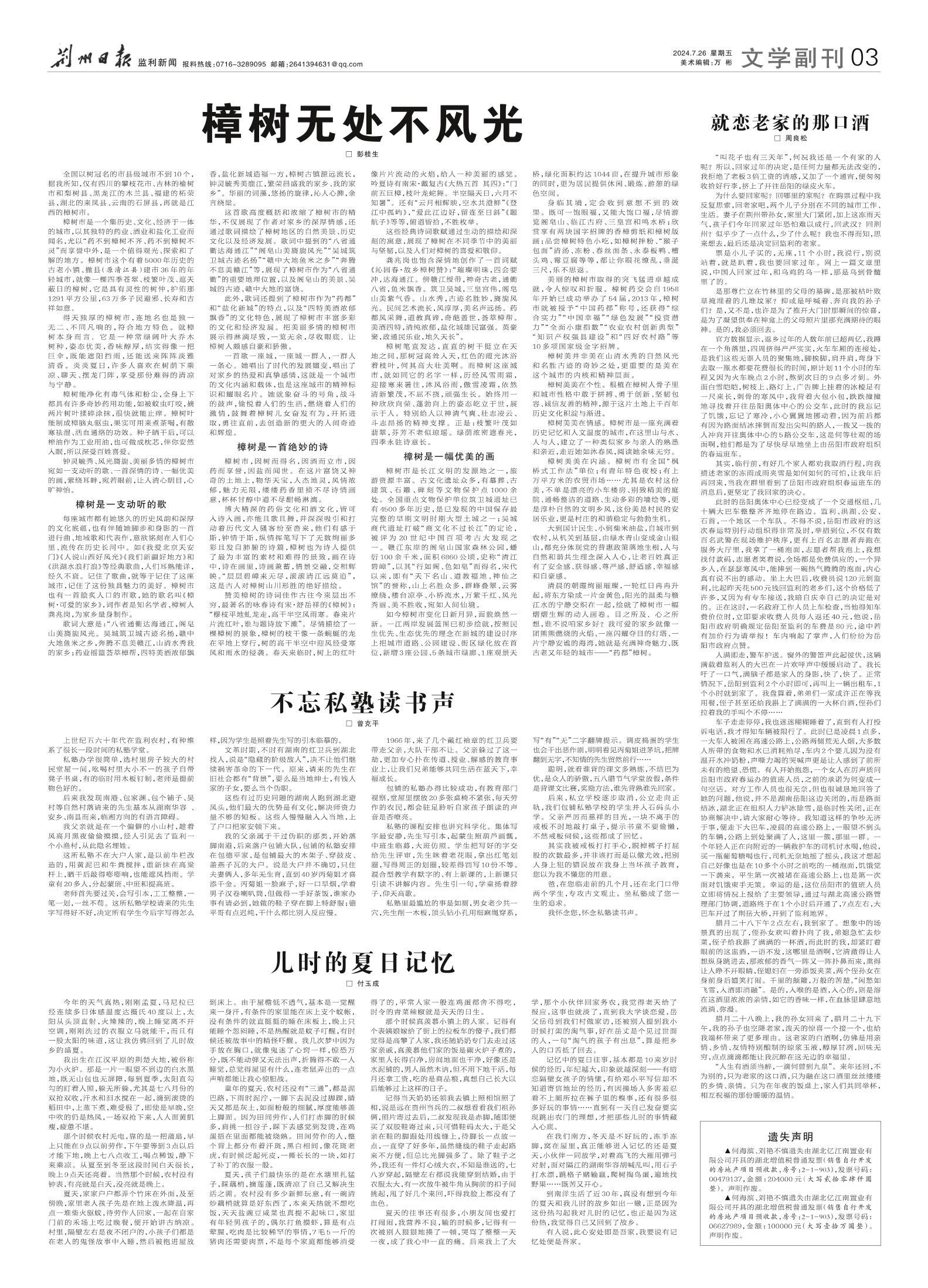□ 曾克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监利农村,有种维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私塾学堂。
私塾办学很简单,选村里房子较大的村民堂屋一间,吆喝村里大小不一的孩子自带凳子书桌,有的临时用木板钉制,老师是提前物色好的。
后来我发现南港、包家渊、包个铺子、吴村等自然村落请来的先生基本从湖南华容、安乡、南县而来,临湘方向的有语言障碍。
我父亲就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趁着风高月黑夜偷偷摸摸,经人引见去了监利一个小渔村,从此隐名埋姓。
这所私塾不在大户人家,是以前牛栏改造的,用黄泥巴和牛粪搅拌,重新抹在高粱杆上,晒干后敲得嘭嘭响,也能遮风挡雨。学童有20多人,分起蒙班、中班和提高班。
老师首先要过关,会写引本,工工整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这所私塾学校请来的先生字写得好不好,决定所有学生今后字写得怎么样,因为学生是照着先生写的引本临摹的。
文革时期,不时有湖南的红卫兵到湖北找人,说是“隐藏的阶级敌人”,决不让他们继续祸害革命的下一代。原来,请来的先生在旧社会都有“背景”,要么是当地绅士,有钱人家的子女,要么当个伪职。
这些有过历史问题的湖南人跑到湖北避风头,他们最大的优势是有文化,解决师资力量不够的短板。这些人慢慢融入入当地,上了户口把家安顿下来。
我的父亲属于干过伪职的那类,开始落脚南港,后来落户包铺大队,包铺的私塾安排在包德平家,是包铺最大的木架子、穿鼓皮、盖燕子瓦的大户。说是大户并不确切,只住夫妻俩人,多年无生育,直到40岁丙菊姐才喜添千金。丙菊姐一脸麻子,好一口旱烟,学着男子汉卷喇叭筒,但做得一手好茶饭,谁家办事有请必到,她做的鞋子穿在脚上特舒服;德平哥有点迟纯,干什么都比别人反应慢。
1966年,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要带走父亲,大队干部不让。父亲躲过了这一劫,更加专心扑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事业上,让我们兄弟能够共同生活在蓝天下,幸福成长。
包铺的私塾办得比较成功,有教育部门视察,堂屋里摆放20多张桌椅不紧张,每天劳作的农民,都会驻足聆听自家孩子朗读的声音是否嘹亮。
私塾的课程安排也讲究科学化。集体写字最安静,先生写引本,起蒙生照葫芦画瓢,中班生临募,大班仿照。学生把写好的字交给先生评审,先生眯着老花眼,拿出红笔划圈,写得周正的划圈,较差得罚写10份不等。混合型教学有默字的、有上新课的,上新课只引读不讲解内容。先生引一句,学童扬着脖子,仰天高歌。
私塾里最尴尬的事是如厕,男女老少共一穴,先生削一木板,顶头钻小孔用细麻绳穿系,写“有”“无”二字翻牌提示。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会干出恶作剧,明明看见丙菊姐进茅坑,把牌翻到无字,不知情的先生贸然前行……
聪明,就看谁背的课文多熟练,不结巴为优,是众人的骄傲,五八腊节气学堂放假,条件是背课文比赛,奖励方法,谁先背熟谁先回家。
后来,私立学校逐步取消,公立走向正轨,我们包铺私塾学校的学生并入石码头小学。父亲严厉而慈祥的目光,一块不离手的戒板不时地敲打桌子,提示书童不要偷懒,不然戒板伺候,这些都成了回忆。
其实我被戒板打打手心,脱掉裤子打屁股的次数最多,并非该打而是以儆尤效,把别人身上犯的错误放在我身上当坏孩子教育,您以为我不懂您的用意。
爸,在您临走前的几个月,还在北门口带两个学生,专攻古文观止。坐私塾成了您一生的追求。
我怀念您,怀念私塾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