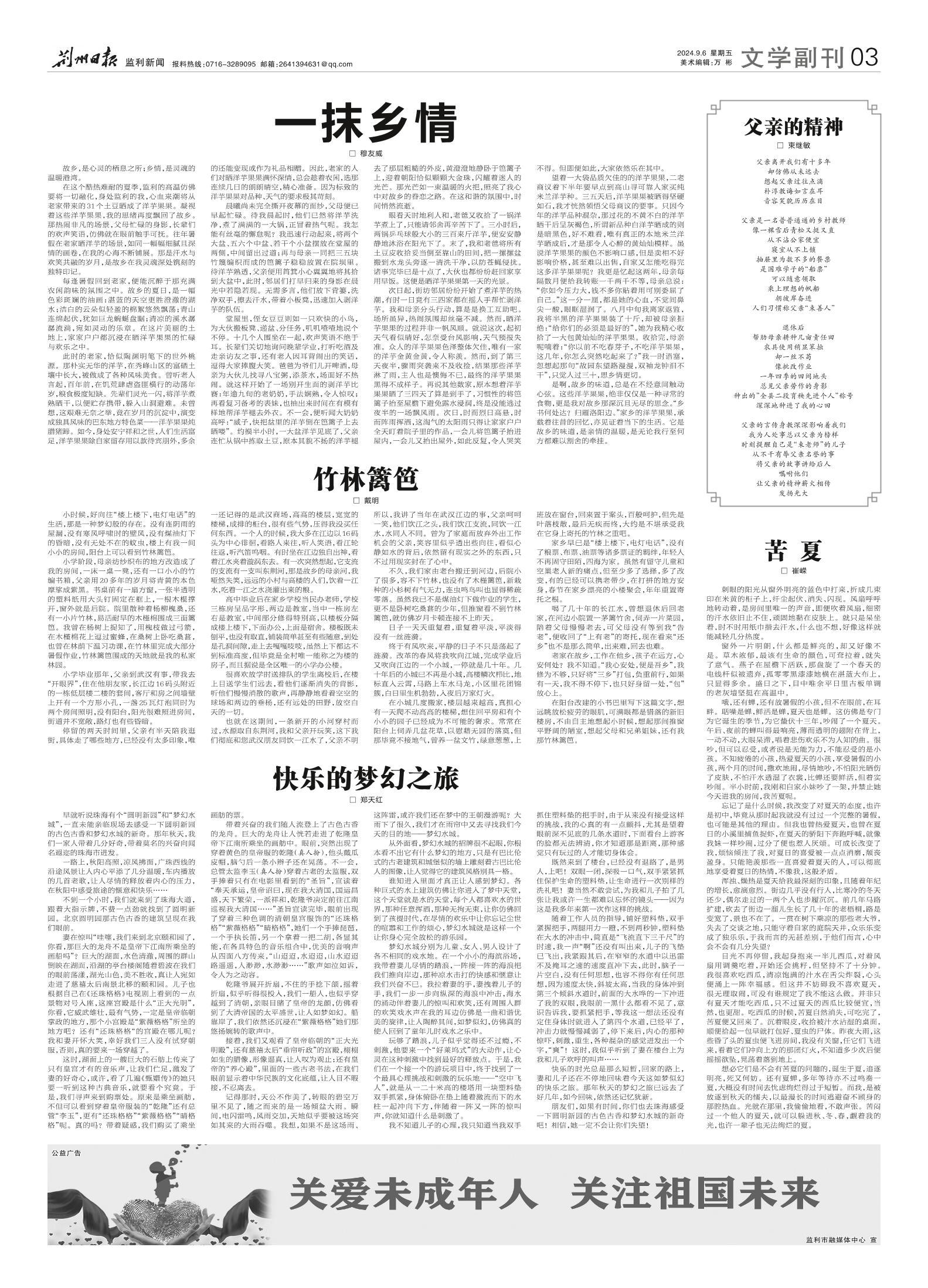□ 戴明
小时候,好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那是一种梦幻般的存在。没有连阴雨的屋漏,没有寒风呼啸时的壁风,没有煤油灯下的昏暗,没有无处不在的蚊虫,楼上有我一间小小的房间,阳台上可以看到竹林篱笆。
小学阶段,母亲纺纱织布的地方改造成了我的房间,一床一桌一凳,还有一口小小的竹编书箱,父亲用20多年的岁月将青黄的本色摩挲成紫黑。书桌前有一扇方窗,一张半透明的塑料纸用大头钉固定在框上,一根木棍撑开,窗外就是后院。院里散种着杨柳槐桑,还有一小片竹林,易活耐旱的木槿棉围成三面篱笆。我曾在杨树上捉知了,用槐枝做过弓箭,在木槿棉花上逗过蜜蜂,在桑树上卧吃桑葚,也曾在林荫下温习功课,在竹林里完成大部分暑假作业,竹林篱笆围成的天地就是我的私家林园。
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到武汉有事,带我去“开眼界”,住在他朋友家,长江边16码头附近的一栋低层楼二楼的套间,客厅和房之间墙壁上开有一个方形小孔,一盏25瓦灯泡同时为两个房间照明,没有阳台,阳光很难照进房间,街道并不宽敞,路灯也有些昏暗。
停留的两天时间里,父亲有半天陪我逛街,具体走了哪些地方,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唯一还记得的是武汉商场,高高的楼层,宽宽的楼梯,成排的柜台,很有些气势,压得我没买任何东西。一个人的时候,我大多在江边以16码头为中心徘徊,看路人来往,听人笑语,看江轮往返,听汽笛呜咽。有时坐在江边独自出神,看着江水夹着漩涡东去。有一次突然想起,它支流的支流有一支叫东荆河,那是故乡的母亲河,我哑然失笑,远远的小村与高楼的人们,饮着一江水,吃着一江之水浇灌出来的粮。
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学校当民办老师,学校三栋房呈品字形,两边是教室,当中一栋房左右是教室,中间部分修得特别高,以楼板分隔成楼上楼下,下面办公,上面是宿舍。楼板既未刨平,也没有取直,铺装简单甚至有些随意,到处是孔洞间隙,走上去嘎嘎吱吱,虽然上下都达不到标准高度,但毕竟是全村唯一能称之为楼的房子,而且据说是全区唯一的小学办公楼。
很喜欢放学时送排队的学生离校后,在楼上目送学生们远去,看他们逐渐消失的背影,听他们慢慢消散的歌声,再静静地看着空空的球场和两边的垂杨,还有远处的田野,放空白天的一切。
也就在这期间,一条新开的小河穿村而过,水源取自东荆河,我和父亲开玩笑,这下我们彻底和您武汉朋友同饮一江水了,父亲不明所以,我讲了当年在武汉江边的事,父亲呵呵一笑,他们饮江之头,我们饮江支流,同饮一江水,水同人不同。曾为了家庭而放弃外出工作机会的父亲,笑容里似乎透出些向往,看似心静如水的背后,依然留有现实之外的东西,只不过用现实封在了心中。
不久,我们家由老台搬迁到河边,后院小了很多,容不下竹林,也没有了木槿篱笆,新栽种的小杉树有气无力,连虫鸣鸟叫也显得稀疏零落。虽然我已不是煤油灯下做作业的学生,更不是卧树吃桑葚的少年,但推窗看不到竹林篱笆,就仿佛岁月卡顿连接不上昨天。
日子一天天重复着,重复着平淡,平淡得没有一丝涟漪。
终于有风吹来,平静的日子不只是荡起了涟漪。改革的春风将我吹向江城,完成学业后又吹向江边的一个小城,一停就是几十年。几十年后的小城已不再是小城,高楼鳞次栉比,地标直入云霄,马路上车水马龙,小区里花团锦簇,白日里生机勃勃,入夜后万家灯火。
在小城几度搬家,楼层越来越高,真担心有一天爬不动高高的楼梯,想住回平房和有个小小的园子已经成为不可能的奢求。常常在阳台上伺弄几盆花草,以慰藉无园的落寞,但那毕竟不接地气,曾养一盆文竹,绿意葱葱,上班放在窗台,回来置于案头,百般呵护,但先是叶落枝散,最后无疾而终,大约是不堪承受我在它身上寄托的竹林之重吧。
家乡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有了粮票、布票、油票等诸多票证的羁绊,年轻人不再固守田陌,四海为家。虽然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新的痛点,但至少多了选择,多了改变,有的已经可以携老带少,在打拼的地方安身,春节在家乡漂亮的小楼聚会,年年重置寄托之根。
喝了几十年的长江水,曾想退休后回老家,在河边小院置一茅篱竹舍,伺弄一片菜园,陪着父母慢慢老去,可父母没有等到我“告老”,便收回了“上有老”的寄托,现在看来“还乡”也不是那么简单,出来难,回去也难。
老家在故乡,工作在他乡,孩子在远方,心安何处? 我不知道。“我心安处,便是吾乡”,我修为不够,只好将“三乡”打包,负重前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停下,也只好身留一处,“包”放心上。
在阳台改建的小书巴里写下这篇文字,想远眺放松疲劳的眼肌,可满眼都是错落的新旧楼房,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想起那间推窗平野阔的陋室,想起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我那竹林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