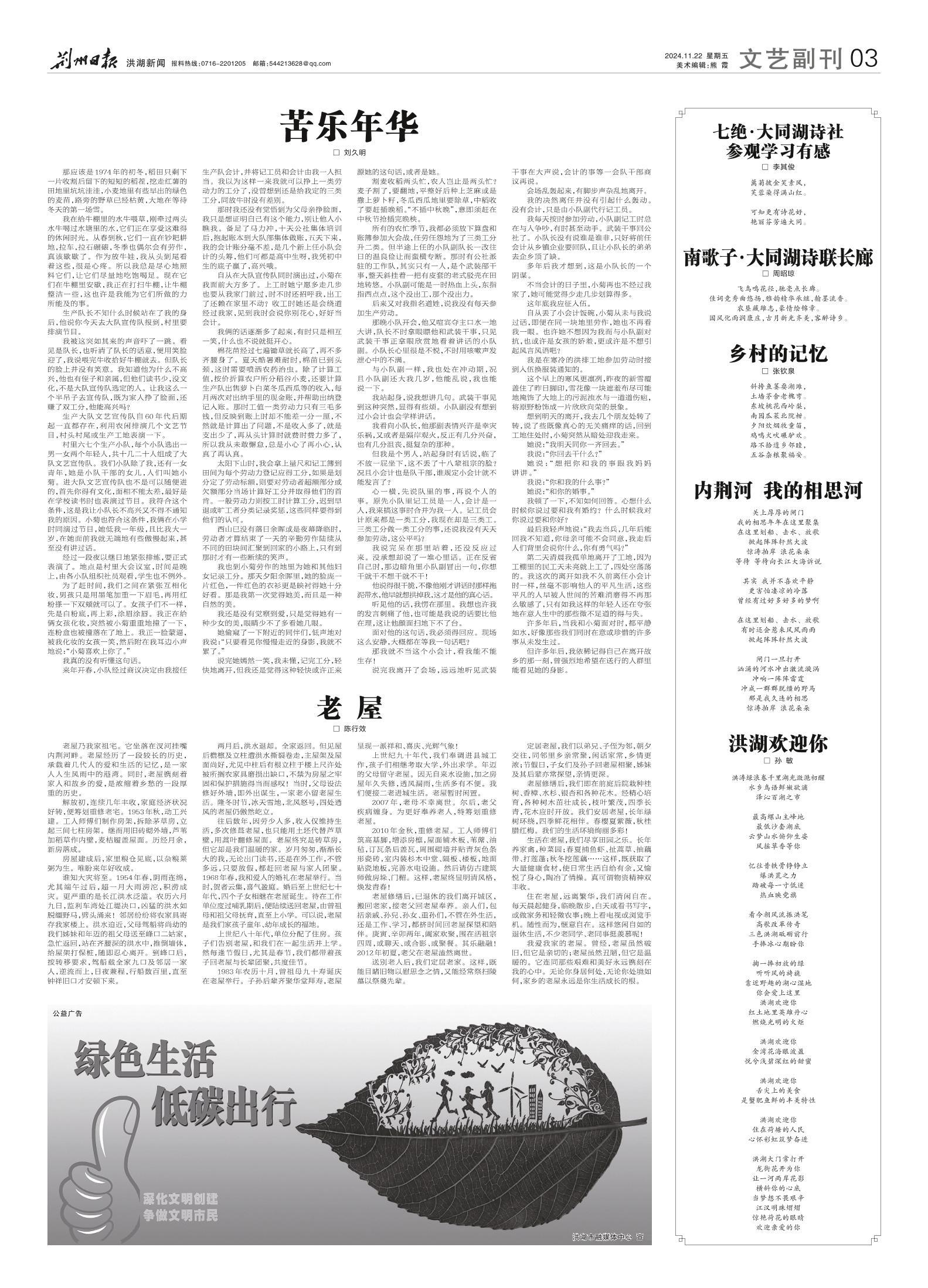□ 陈行效
老屋乃我家祖宅。它坐落在汊河挂嘴内荆河畔。老屋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承载着几代人的爱和生活的记忆,是一家人人生风雨中的港湾。同时,老屋镌刻着家人和故乡的爱,是浓缩着乡愁的一段厚重的历史。
解放初,连续几年丰收,家庭经济状况好转,便筹划重修老宅。1953年秋,动工兴建。工人师傅们制作房架,拆除茅草房,立起三间七柱房架。继而用旧砖砌外墙,芦苇加稻草作内壁,麦桔履盖屋面。历经月余,新房落成。
房屋建成后,家里粮仓见底,以杂粮莱粥为生。唯盼来年好收成。
谁知大灾将至。1954年春,阴雨连绵,尤其端午过后,超一月大雨滂沱,积涝成灾。更严重的是长江洪水泛滥。农历六月九日,监利车湾处江堤决口,凶猛的洪水如脱缰野马,劈头涌来! 邻居纷纷将农家具寄存我家楼上。洪水迫近,父母驾船将尚幼的我们姊妹和年迈的祖父母送至峰口二姑家,急忙返回,站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推倒墙体,给屋架打保桩,随即忍心离开。到峰口后,按转移要求,驾船载全家九口及邻居一家人,逆流而上,日夜兼程,行船数百里,直至钟祥旧口才安顿下来。
两月后,洪水退却。全家返回。但见屋后檐檩及立柱遭洪水撕裂卷走,主屋架及屋面尚好,尤见中柱后有根立柱于楼上尺许处被所搁农家具磨损岀缺口,不禁为房屋之牢固和保护措施得当而感叹! 当时,父母设法修好外墙,即外出谋生,一家老小留老屋生活。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北风怒号,四处透风的老屋仍傲然屹立。
往后数年,因劳少人多,收入仅维持生活,多次修葺老屋,也只能用土坯代替芦草壁,用蒿叶翻修屋面。老屋终究是砖草房,但它却是我们温暖的家。岁月匆匆,渐渐长大的我,无论岀门读书,还是在外工作,不管多远,只要放假,都赶回老屋与家人团聚。1968年春,我和爱人的婚礼在老屋举行。当时,贺者云集,喜气盈庭。婚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四个子女相继在老屋诞生。待在工作单位度过哺乳期后,便陆续送回老屋,由曾祖母和祖父母抚育,直至上小学。可以说,老屋是我们家孩子童年、幼年成长的福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分配了住房。孩子们告别老屋,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并上学。然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我们都带着孩子回老屋与长辈团聚,共度佳节。
1983年农历十月,曾祖母九十寿诞庆在老屋举行。子孙后辈齐聚华堂拜寿,老屋呈现一派祥和、喜庆、光辉气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奉调进县城工作,孩子们相继考取大学,外岀求学。年迈的父母留守老屋。因无自来水设施,加之房屋年久失修,透风漏雨,生活多有不便。我们便接二老进城生活。老屋暂时闲置。
2007年,老母不幸离世。尔后,老父疾病缠身。为更好奉养老人,特筹划重修老屋。
2010年金秋,重修老屋。工人师傅们筑高基脚,增添房檩,屋面铺木板、苇蓆、油毡,订瓦条后盖瓦,周围砌墙并贴青灰色条形瓷砖,室内装杉木中堂、隔板、楼板,地面贴瓷地板,完善水电设施。然后请仿古建筑师做房垛、门楣。这样,老屋终显明清风格,焕发青春!
老屋修缮后,已退休的我们离开城区,搬回老家,接老父回老屋奉养。亲人们,包括亲戚、孙兒、孙女、重孙们,不管在外生活,还是工作、学习,都挤时间回老屋探望和陪伴。庚寅、辛卯两年,阖家欢聚,围在活祖宗四周,或聊天、或合影、或聚餐。其乐融融!2012年初夏,老父在老屋溘然离世。
送别老人后,我们定居老家。这样,既能目睹旧物以慰思念之情,又能经常祭扫陵墓以祭奠先辈。
定居老屋,我们以弟兄、子侄为邻,朝夕交往,同邻里乡亲常聚,闲话家常,乡情更浓;节假日,子女们及孙子回老屋相聚,姊妹及其后辈亦常探望,亲情更深。
老屋修缮后,我们即在前庭后院栽种桂树、香樟、水杉、银杏和各种花木。经精心培育,各种树木茁壮成长,枝叶繁茂,四季长青,花木应时开放。我们安居老屋,长年绿树环绕,四季鲜花相伴。春樱夏紫薇,秋桂腊红梅。我们的生活环境绚丽多彩!
生活在老屋,我们尽享田园之乐。长年养家禽,种菜园;春夏捕鱼虾、扯蒿草、抽藕带、打莲蓬;秋冬挖莲藕……这样,既获取了大量健康食材,使日常生活自给有余,又愉悦了身心,陶冶了情操。真可谓物资精神双丰收。
住在老屋,远离繁华,我们清闲自在。每天晨起健身,临晚散步,白天或看书写字,或做家务和轻微农事;晚上看电视或浏览手机。随性而为,惬意自在。这样悠闲自如的退休生活,不少老同学、老同事挺羡慕呢!
我爱我家的老屋。曾经,老屋虽然破旧,但它是亲切的;老屋虽然丑陋,但它是温暖的。它连同那些艰难和美好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无论你身居何处,无论你处境如何,家乡的老屋永远是你生活成长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