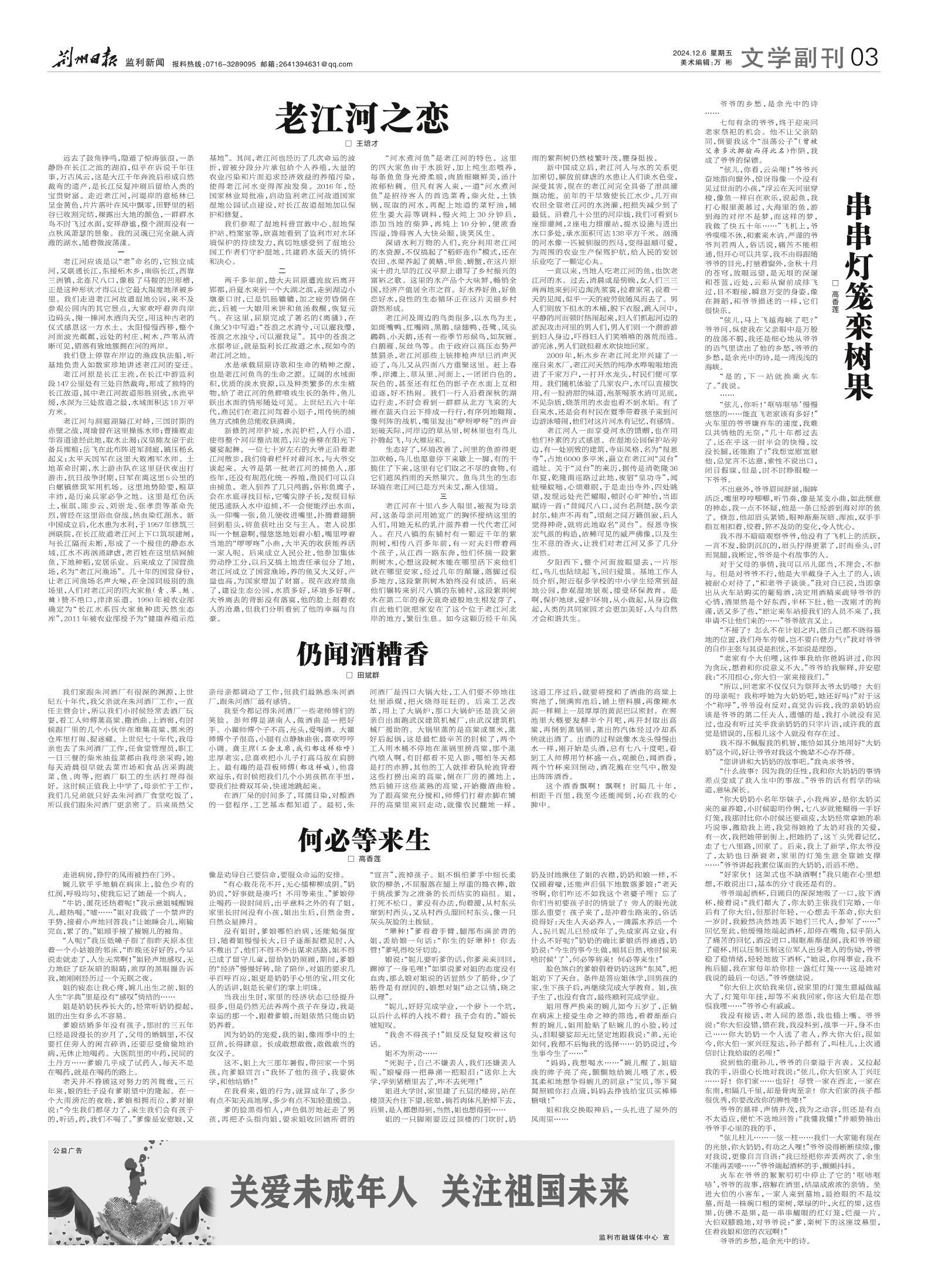□ 王培才
远去了鼓角铮鸣,隐遁了惊涛骇浪,一条静卧在长江之滨的湖泊,似乎在诉说千年往事,万古风云,这是大江千年奔流后形成自然裁弯的遗产,是长江反复冲刷后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走近老江河,河堤岸的意杨林已呈金黄色,片片落叶在风中飘零,田野里的稻谷已收割完结,裸露出大地的颜色,一群群水鸟不时飞过水面,安祥静谧,整个湖面没有一点秋风萧瑟的景象。我的灵魂已完全融入清澈的湖水,随着微波荡漾。
一
老江河应该是以“老”命名的,它独立成河,又联通长江,东接柘木乡,南临长江,西靠三洲镇,北连尺八口,像极了马鞍的凹形槽,正是这种形状才得以让它最大限度地泽被乡里。我们走进老江河故道湿地公园,来不及参观公园内的其它景点,大家欢呼着奔向岸边码头,掬一捧河水洒向天空,用这种古老的仪式感恩这一方水土。太阳慢慢西移,整个河面波光粼粼,远处的村庄、树木、芦苇丛清晰可见,错落有致地簇拥在河的两岸。
我们登上停靠在岸边的渔政执法船,听基地负责人如数家珍地讲述老江河的变迁。
老江河原是长江主流,在长江中游监利段147公里处有三处自然裁弯,形成了独特的长江故道,其中老江河故道形胜别致,水流平缓,水深为三处故道之最,水域面积达18万平方米。
老江河与洞庭湖隔江对峙,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周瑜曾在这里操练水师;曹操败走华容道途经此地,取水止渴;汉皇陈友谅于此备兵囤粮;岳飞在此布阵进军洞庭,镇压杨幺起义;太平天国军在这里大败湘军水师。土地革命时期,水上游击队在这里昼伏夜出打游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离这里5公里的白螺镇修筑军用机场。这里地势险要,粮草丰沛,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红色沃土,崔琪、陈步云、刘崇龙、张孝贵等革命先烈,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热血染红湖水。新中国成立后,化水患为水利,于1957年修筑三洲联院,在长江故道老江河上下口筑坝建闸,与长江隔而未断,形成了一个极佳的静态水域,江水不再汹涌肆虐,老百姓在这里结网捕鱼,下地种稻,安居乐业。后来成立了国营渔场,名为“老江河渔场”。几十年的国营身份,让老江河渔场名声大噪,在全国同级别的渔场里,人们对老江河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赞不绝口,津津乐道。1990年被农业部确定为“长江水系四大家鱼种质天然生态库”,2011年被农业部授予为“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其间,老江河也经历了几次命运的波折,曾被分段分片承包给个人养殖,大量的农业污染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养殖污染,使得老江河水变得浑浊发臭。2016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启动监利老江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对长江故道湿地加以保护和修复。
我们参观了湿地科普宣教中心、湿地保护站、档案室等,欣喜地看到了监利市对水环境保护的持续发力,真切地感受到了湿地公园工作者们守护湿地、共建碧水蓝天的情怀和决心。
二
两千多年前,楚大夫屈原遭流放后离开郢都,沿夏水来到一个大湖之滨,走到湖边小墩豪口时,已是饥肠辘辘,加之疲劳昏倒在此,后被一大娘用米饼和鱼汤救醒,恢复元气。在这里,屈原完成了著名的《离骚》,在《渔父》中写道:“苍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苍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其中的苍浪之水据考证,就是监利长江故道之水,现如今的老江河之地。
水是承载屈原诗歌和生命的精神之源,也是老江河鱼鸟的生命之源。辽阔的水域面积,优质的淡水资源,以及种类繁多的水生植物,给了老江河的鱼群嘻戏生长的条件,鱼儿跃出水面的情形随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渔民们在老江河驾着小划子,用传统的捕鱼方式捕鱼总能收获满满。
新修的河岸护坡,水泥护栏,人行小道,使得整个河岸整洁规范,岸边垂柳在阳光下婆娑起舞。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大爷正沿着老江河散步,我们倚着栏杆对着河水,与大爷交谈起来。大爷是第一批老江河的捕鱼人,那些年,还没有规范化统一养殖,渔民们可以自由捕鱼。老人驯养了几只鸬鹚,俗称鱼鹰子,会在水底寻找目标,它嘴尖脖子长,发现目标便迅速跃入水中追捕,不一会便能浮出水面,头一仰嘴一张,鱼儿便收进嘴里,扑腾着翅膀回到船头,将鱼获吐出交与主人。老人说那叫一个惬意啊,慢悠悠地划着小船,嘴里哼着当地的“啰啰咚”小曲,大半天的收获能养活一家人呢。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他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以后又搞土地责任承包分了地,老江河成立了国营渔场,养的鱼又大又好,产量也高,为国家增加了财富。现在政府禁渔了,建设生态公园,水质多好,环境多好啊。大爷离去的背影没有落寞,他的脸上刻着农人的沧桑,但我们分明看到了他的幸福与自豪。
“河水煮河鱼”是老江河的特色。这里的四大家鱼由于水质好,加上纯生态喂养,每条鱼鱼身光滑柔顺,肉质细嫩鲜美,汤汁浓郁粘稠。但凡有客人来,一道“河水煮河鱼”是招待客人的首选菜肴,柴火灶,土铁锅,现取的河水,再配上地道的菜籽油,辅佐生姜大蒜等调料,慢火炖上30分钟后,添加当地的柴笋,再炖上10分钟,便浓香四溢,馋得客人大快朵颐,谈笑风生。
深谙水利万物的人们,充分利用老江河的水资源,不仅搞起了“稻虾连作”模式,还在农田、水渠养起了黄鳝、甲鱼、螃蟹,在这片原来十涝九旱的江汉平原上谱写了乡村振兴的富裕之歌。这里的水产品个大味鲜,畅销全国,经济产值居全市之首。好水养好鱼,好鱼恋好水,良性的生态循环正在这片美丽乡村蔚然形成。
老江河及周边的鸟类很多,以水鸟为主,如斑嘴鸭、红嘴鸥、黑鹅、绿翅鸭、苍鹭、凤头鸊鹈、小天鹅,还有一些季节形候鸟,如灰雁、白鹅雁、灰丝鸟等。由于政府以高压态势严禁猎杀,老江河那些土铳排枪声早已消声灭迹了,鸟儿又从四面八方重聚这里。赶上春季,岸滩上、草从里、河面上,一团团白色的,灰色的,甚至还有红色的影子在水面上互相追逐,好不热闹。我们一行人沿着深秋的湖边行走,不时会看到一群群从北方飞来的大雁在蓝天白云下排成一行行,有序列地翱翔,像列阵的战机,嘴里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划破天际,河岸边的草丛里,树林里也有鸟儿扑腾起飞,与大雁应和。
生态好了,环境改善了,河里的鱼游得更加欢畅,鸟儿也愿意停下来歇上一脚,有的干脆住了下来,这里有它们取之不尽的食物,有它们遮风挡雨的天然巢穴。鱼鸟共生的生态环境在老江河已是方兴未艾,渐入佳境。
三
老江河在十里八乡人眼里,被视为母亲河,这条母亲河用她宽广的胸怀接纳这里的人们,用她无私的乳汁滋养着一代代老江河人。在尺八镇的东铺村有一颗近千年的紫荆树,相传八百多年前,有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从江西一路东奔,他们怀揣一段紫荆树木,心想这段树木能在哪里活下来他们就在哪里安家,经过几年的颠簸,落脚过很多地方,这段紫荆树木始终没有成活。后来他们辗转来到尺八镇的东铺村,这段紫荆树木在第二年的春天竟奇迹般地生根发芽了,自此他们就把家安在了这个位于老江河北岸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这颗历经千年风雨的紫荆树仍然枝繁叶茂,腰身挺拔。
新中国成立后,老江河人与水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前肆虐的水患让人们谈水色变,深受其害,现在的老江河完全具备了泄洪灌溉功能。前年的干旱致使长江水少,几万亩农田全靠老江河的水浇灌,把损失减少到了最低。沿着几十公里的河岸线,我们可看到5座排灌闸,2座电力排灌站,提水设施与进出水口多处,承水面积可达138平方千米。汹涌的河水像一匹被驯服的烈马,变得温顺可爱,为周围的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给人民的安居乐业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直以来,当地人吃老江河的鱼,也饮老江河的水。过去,清晨或是傍晚,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河边淘洗浆裳,拉着家常,说着一天的见闻,似乎一天的疲劳就随风而去了。男人们则放下担水的木桶,脱下衣服,跳入河中,平静的河面顿时热闹起来,妇人们抓起河边的淤泥攻击河里的男人们,男人们则一个潜游游到妇人身边,吓得妇人们笑嘻嘻的落荒而逃。游完泳,男人们就担着水欢快地回家。
2009年,柘木乡在老江河北岸兴建了一座自来水厂,老江河天然的纯净水哗啦啦地流进了千家万户,一打开水龙头,村民们便可享用。我们随机体验了几家农户,水可以直接饮用,有一股清甜的味道,泡茶喝茶水清可见底,不见杂质,烧茶用的水壶也看不到水垢。有了自来水,还是会有村民在夏季带着孩子来到河边游泳嘻闹,他们对这片河水有记忆,有感情。
老江河人一面享受河水的馈赠,也在用他们朴素的方式感恩。在湿地公园保护站旁边,有一处别致的建筑,寺庙风格,名为“报恩寺”,占地6000多平米,矗立在老江河“灵台”遗址。关于“灵台”的来历,据传是清乾隆36年夏,乾隆南巡路过此地,夜宿“皇功寺”,闻蛙噪蚊嗡,心烦难眠,于是走出寺外,四处眺望,发现远处光芒耀眼,顿时心旷神怡,当即赋诗一首:“昔闻尺八口,灵台名荆楚,朕今亲封尔,蛙声不再有”,顷刻之间万籁俱寂,后人觉得神奇,就将此地取名“灵台”。报恩寺恢宏气派的构造,依稀可见的威严佛像,以及生生不息的香火,让我们对老江河又多了几分肃然。
夕阳西下,整个河面放眼望去,一片彤红,鸟儿也陆续起飞,回归爱巢。基地工作人员介绍,附近很多学校的中小学生经常到湿地公园,参观湿地景观,接受环保教育。是啊,保护地球,爱护环境,从小做起,从身边做起,人类的共同家园才会更加美好,人与自然才会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