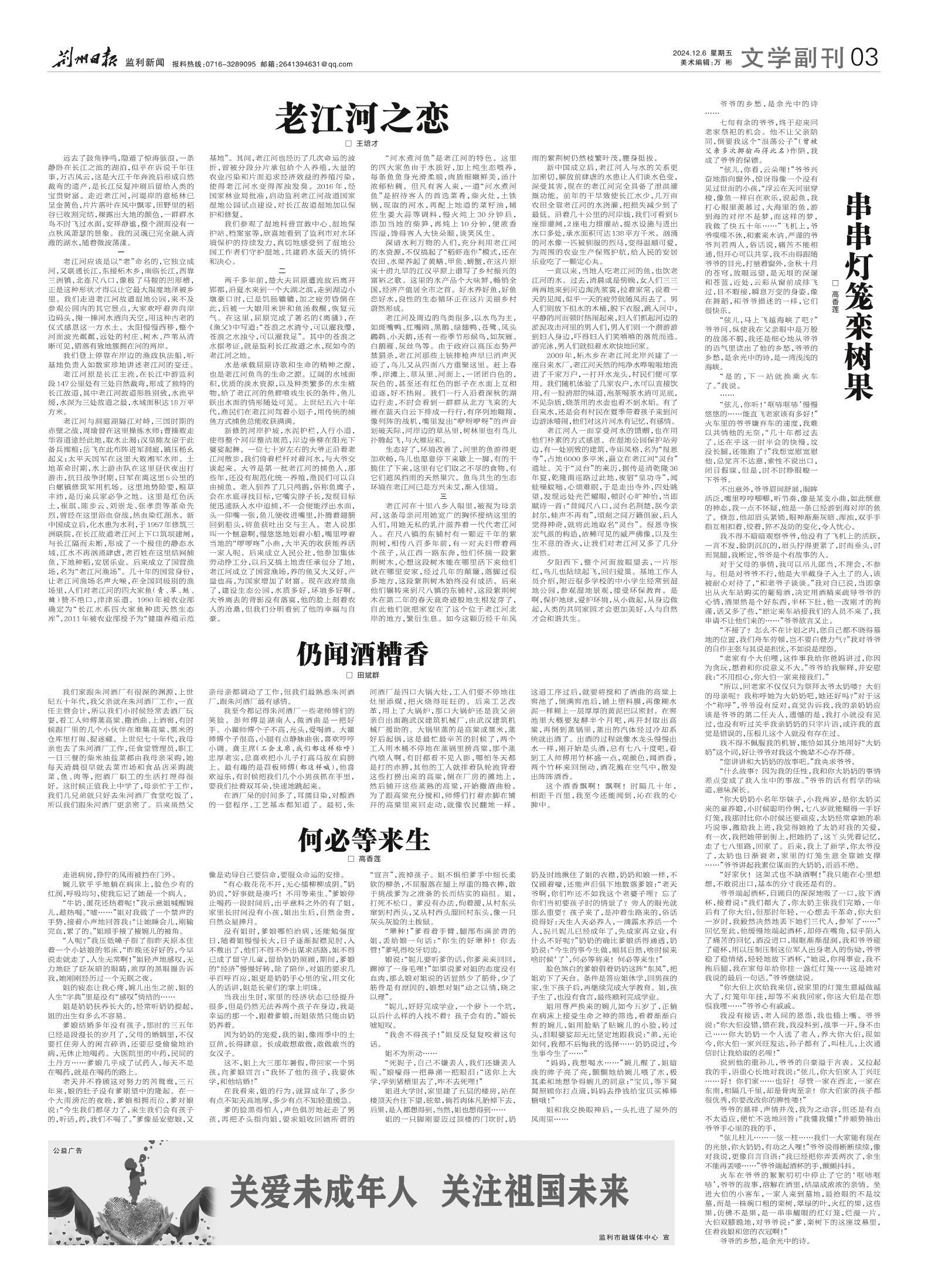□ 田斌群
我们家跟朱河酒厂有很深的渊源,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就在朱河酒厂工作,一直任主管会计,所以我们小时候经常去酒厂玩耍,看工人师傅蒸高粱、撒酒曲、上酒窖,有时候跟厂里的几个小伙伴在堆集高粱、粟米的仓库里打闹、捉迷藏。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母亲也去了朱河酒厂工作,任食堂管理员,职工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菜都由我母亲采购,她每天清晨很早就去菜市场和食品店采购蔬菜、鱼、肉等,把酒厂职工的生活打理得很好。这时候正值我上中学了,母亲忙于工作,我们几兄弟就只好去朱河酒厂食堂吃饭了,所以我们跟朱河酒厂更亲密了。后来虽然父亲母亲都调动了工作,但我们最熟悉朱河酒厂,跟朱河酒厂最有感情。
我至今都记得朱河酒厂一些老师傅们的笑脸。彭师傅是湖南人,做酒曲是一把好手。小瞿师傅个子不高,光头,爱喝酒。大瞿师傅个子很高,小腿有点静脉曲张,喜欢哼哼小调。龚主席(工会主席,我们都这样称呼)忠厚老实,总喜欢把小儿子打高马放在肩膀上。最有趣的是苕板师傅(都这样喊),他喜欢逗乐,有时候把我们几个小男孩抓在手里,要我们扯着双耳朵,快速地跳起来。
在酒厂呆的时间多了,耳濡目染,对酿酒的一套程序、工艺基本都知道了。最初,朱河酒厂是四口大锅大灶,工人们要不停地往灶里添煤,把火烧得旺旺的。后来工艺改革,用上了大锅炉,那口大锅炉还是我父亲亲自出面跑武汉建筑机械厂,由武汉建筑机械厂援助的。大锅里蒸的是高粱或粟米,蒸好后起锅,这是最忙最辛苦的时候了,两个工人用木桶不停地在蒸锅里捞高粱,那个蒸汽喷人啊,有时都看不见人影,哪怕冬天都是打的赤膊,其他的工人就排着队轮流背着这些打捞出来的高粱,倒在厂房的摊地上,然后铺开这些蒸熟的高粱,开始撒酒曲粉。为了跟高粱充分搅和,师傅们打着赤脚在铺开的高粱里来回走动,就像农民翻地一样。这道工序过后,就要将搅和了酒曲的高粱上窖池了,倒满窖池后,铺上塑料膜,再像糊水泥一样糊上一层厚厚的黄泥巴以密封。在窖池里大概要发酵半个月吧,再开封取出高粱,再倒到蒸锅里,蒸出的汽体经过冷却系统就出酒了。出酒的过程就像水龙头慢慢出水一样,刚开始是头酒,总有七八十度吧,看到工人师傅用竹杯盛一点,观颜色,闻酒香,两个竹杯来回倒动,酒花溅在空气中,散发出阵阵酒香。
这个酒香飘啊! 飘啊! 时隔几十年,相距千百里,我至今还能闻到,沁在我的心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