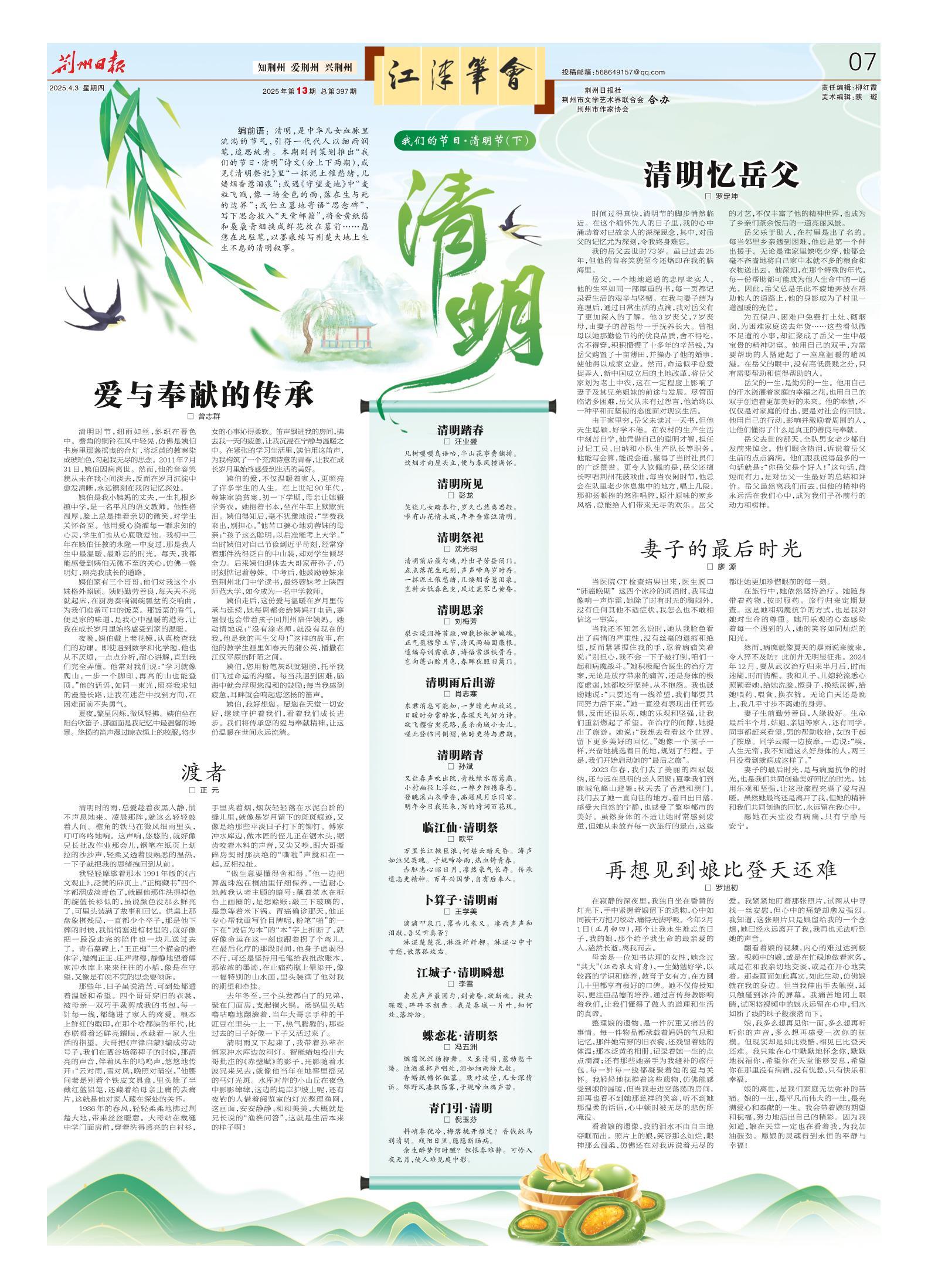□ 正元
清明时的雨,总爱趁着夜黑人静,悄不声息地来。凌晨那阵,就这么轻轻敲着人间。檐角的铁马在微风细雨里头,叮叮咚咚地响。这声响,悠悠的,就好像兄长批改作业那会儿,钢笔在纸页上划拉的沙沙声,轻柔又透着股熟悉的温热,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拽回到从前。
我轻轻摩挲着那本1991年版的《古文观止》,泛黄的扉页上,“正梅藏书”四个字都洇成淡青色了,就跟他那件洗得掉色的靛蓝长衫似的,虽说颜色没那么鲜亮了,可里头装满了故事和回忆。供桌上那盘象棋残局,一直都少个卒子,那是他下葬的时候,我悄悄塞进棺材里的,就好像把一段没走完的陪伴也一块儿送过去了。青石墓碑上,“王正梅”三个描金的楷体字,端端正正、庄严肃穆,静静地望着傅家冲水库上来来往往的小船,像是在守望,又像是有说不完的思念要倾诉。
那些年,日子虽说清苦,可到处都透着温暖和希望。四个哥哥穿旧的衣裳,被母亲一双巧手裁剪成我的书包,每一针每一线,都缝进了家人的疼爱。粮本上鲜红的戳印,在那个啥都缺的年代,比春联看着还鲜亮耀眼,承载着一家人生活的指望。大哥把《声律启蒙》编成劳动号子,我们在晒谷场筛稗子的时候,那清亮的声音,伴着风车的呜呜声,悠悠地传开:“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他腰间老是别着个铁皮文具盒,里头除了半截红蓝铅笔,还藏着给母亲止痛的去痛片,这就是他对家人藏在深处的关怀。
1986年的春风,轻轻柔柔地拂过荆楚大地,带来丝丝暖意。大哥站在裁缝中学门面房前,穿着洗得透亮的白衬衫,手里夹着烟,烟灰轻轻落在水泥台阶的缝儿里,就像是岁月留下的斑斑痕迹,又像是给那些平淡日子打下的铆钉。傅家冲水库边,做木匠的侄儿正在锯木头,锯齿咬着木料的声音,又尖又吵,跟大哥撕碎房契时那决绝的“嘶啦”声搅和在一起,互相拉扯。
“做生意要懂得舍和得。”他一边把算盘珠泡在桐油里仔细保养,一边耐心地教我认老主顾的暗号:蘸着茶水在柜台上画圈的,是想赊账;敲三下玻璃的,是急等着米下锅。胃癌确诊那天,他正专心帮我重写价目牌呢,粉笔“啪”的一下在“诚信为本”的“本”字上折断了,就好像命运在这一刻也跟着拐了个弯儿。在最后化疗的那段时间,他身子虚弱得不行,可还是坚持用毛笔给我批改账本,那浓浓的墨迹,在止痛药瓶上晕染开,像一幅特别的山水画,里头装满了他对我的期望和牵挂。
去年冬至,三个头发都白了的兄弟,聚在门面房,支起铜火锅。汤锅里头咕噜咕噜地翻滚着,当年大哥亲手种的干豇豆在里头一上一下,热气腾腾的,那些过去的日子好像一下子又活过来了。
清明雨又下起来了,我带着孙辈在傅家冲水库边放河灯。智能蜡烛投出大哥批注的《赤壁赋》的影子,光影随着水波晃来晃去,就像他当年在地窖里摇晃的马灯光斑。水库对岸的小山丘在夜色中影影绰绰,这边的堤岸护坡上呢,还有夜钓的人借着阅览室的灯光整理渔网,这画面,安安静静、和和美美,大概就是兄长说的“渔樵问答”,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