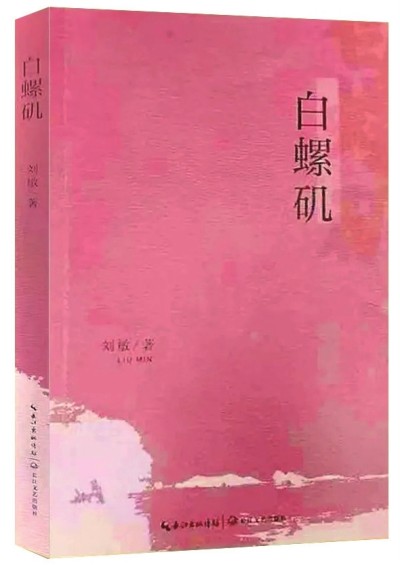口 李雁
近日,阅读监利诗人刘敏新诗集《白螺矶》,感受颇多。诗集收录了刘敏自2019年至2024年间诗歌作品216首,每首诗都是他情感的真实映射,是他这5年间所思所想,是他五年间想到的每一个人,是他5年间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全书分为望黄昏、广济桥、缝隙、穿越四辑。
第一辑“望黄昏”主要写人。以母亲为主题的诗最多,似乎所有的场景都会让诗人想起母亲。母亲的意象无处不在:五里庙、黄昏、干萝卜、油灯、顶针、甚至是一句谚语“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些意象,都是诗人生活中最熟悉的场景、物件,可见,只要回望这些记忆,母亲就从他心中跳出来。“母亲脚小量了整整五十年”“只有深深的黄昏/才能把母亲带回家”“母亲带哭的嘶喊喊我回家/像一盏油灯艰难地把黑暗喊亮”“她一步步后退,又像一步步朝前/走进我的书本/走进句寓言”“这枚小小的顶针/里面藏着一个人,布满针坑的一生”……这些诗句,触及到读者最柔软的部分,令读者毫无抵抗力,引起强烈共鸣,有时甚至不忍卒读。
父亲、妻子、儿女、国青叔、孟秋、金春姑妈,都是诗人最亲的人,诗人的笔下饱蘸深情的字句都送给了他们。我们认识了“用一根粗草绳捆紧棉袄捆紧腰的父亲”,认识了为他哭的大嫂、关秀姐、姑妈金春,还有像地米花一样美好的妻,像“前世的债主”女儿,这些都是诗人一生割舍不下的亲人,他对他们的爱,厚重得读者无托举之力。
第二辑“广济桥”收录了诗人68首诗,占四辑比重最大,是一组关于行走的诗。翻阅着这些诗,仿佛展开了一幅幅画卷。它们是北京、深圳、潮州、台州、西藏、老江河、柘木……从城市到乡村,从草原到古城,从一座楼到一棵树,从一条河到一座桥,密密布满了诗人行走足迹。诗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清华园、深圳、监利,因为清华园是女儿工作之地,深圳是儿子居住之地,而监利是他的根,循着诗人的足迹,读者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读到的仍旧是满满的深情。《卢沟桥》《一多》《登岳阳楼》《漳河行》《监利剅口,无名烈士碑》《丁家洲碉堡》等体现了诗人的家国情怀,《深圳灯光秀》《清华学堂》呈现了美好的希望、岁月静好。
最多的笔墨,诗人留给了故土。老江湖、白螺矶、林长河、滨江公园、狮子山、杨林山、丁家洲、柘木,这些熟悉的地名,在诗人笔下蕴含诗意,情、景、人交融。诗人以散文诗形态展开叙事,赋予诗歌更大的表达空间。“如果一直坐下去,我就要/把长江坐老把矶石坐老”,极有张力的诗句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这辑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记录,也是对乡土文化的致敬。
《缝隙》这个题目我很喜欢,诗人用作第三辑名。这辑多写小人物,还收录了写给朋友同学的诗。剪刀唐、陈年酒坊老板、卖饺子猪肝汤的熊妑妑、擦皮鞋的老许,还有爱吃糖的女孩,卖哈密瓜的夫妇、倚靠栏杆着工装的老人、行走在街巷闾里的补漏者,这些被忽略的人小物一个个跳进他的诗中,放大镜般再现他们的装束、神态、动作。不得不佩服诗人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警察职业习惯,也许就是一个诗人独特视角。透过这视角,读者看到了一个深怀悲悯情怀的诗人,他行走在大街小巷,目光探寻到一道道缝隙,捕捉到缝隙中平凡的仍为生存而努力的人们。如《补漏者》核心意象是“漏洞”,既指物理的房屋渗漏,也象征生活中的问题和缺憾。通过补漏者的日常,揭示了城市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用具体的意象隐喻生活的漏洞与无奈,结构自由而富有层次,语言平实中蕴含深意,成功地将个人经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穿越》这辑诗充满了生命哲思。《疤痕》组诗中,诗人将对木、绳、水、火、日与目、木与林等的直观感受,通过敏锐的感知,将复杂现实生活凝练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诗歌意象,构建出独特的诗歌意境。“木”毁灭自己,成为桥、舟、轮子、火,为人所用;绳把结打在自己身上,同时也把结打在人身上,这是一种相互束缚;火烧伤的总是别人,人类发火却总是先烧到自己;上天用太阳看人类、看万物,人却用两只眼睛看上天、看世界、看自己,这种相互观望暗示着自省。走《玻璃桥》,诗人领悟到“把自己悬挂在深渊之上/事先设想过最坏的结果/心情才会像湖面一样平静”;《一瓢水》让一块半边裸的石头完成了圆满;《留白》“与黑没有关系”“空白也不是白”……这样的哲思妙语在本辑中随处可见,像一颗颗星子,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整部诗集以丰富的意象、凝练的语言与开放的结构,触及到亲人、地域、小人物、生命哲思等广泛主题。诗人刘敏仿佛从故乡站立起来,一步步向前走,越走越远,越走越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