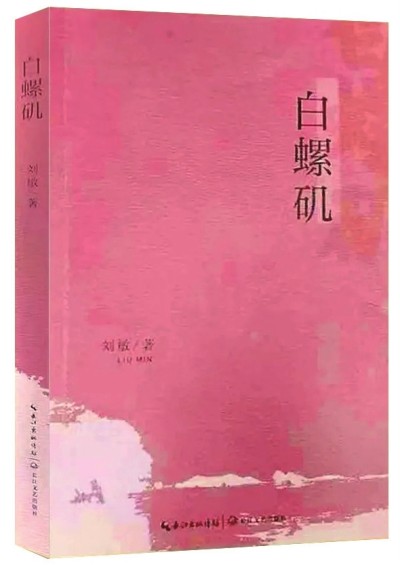口 刘赋
今年2月,监利诗人刘敏的诗集《白螺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这部诗集,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题材涵盖乡土书写、父母亲恩、山川游历、管鲍之交、历史钩沉、人文探幽、舐犊深情、交颈之爱、懵懂青葱、市井烟火、百业镜像、世界风云、地缘政治、球类竞技、幽居心声。该诗集形式上既有沉郁顿挫的长卷抒情与叙事体诗歌,又有风格清新、节奏明快的类似于绝句、小令体的短章,更多的是刘敏十分擅长、驾轻就熟、常写常新的类“十四行体”诗歌。他在诗歌的形式上大胆进行探索,在题材的广度上不断拓展,尤其是在语言的锤炼与打磨上,更是下了大功夫。刘敏对诗歌艺术的那份执着、坚韧、勤奋与付出,还有自信,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动之余,有时候,也还为他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诗歌所受到的冷遇而感到内心隐隐。
近些年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刘敏重操旧业,或者说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同自己较劲,与时间赛跑,集中写出了一大批诗作。在故乡的小县城内,刘敏属于是能文能武、文武兼备、小有成功的才子人物。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诗歌的土壤最为丰厚与广博,诗歌(包括民歌)创作也十分亲民(门槛不高),但想要独出机杼、写出新意,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刘敏青年时期的作品,与热情高涨的改革开放大潮相伴相生,以浪漫热烈、直抒胸臆、辞藻华丽、铺陈排比为主;到了壮年时期,在保留一如既往的充沛激情与炫目修辞格的同时,在诗歌表达的内容与题材上,则更多聚焦民生的艰辛与生活的复杂与多样性,一承《国风》与《行路难》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永葆理想与激情的同时,对人生如弈棋、一言难尽、欲说还休有了更多的体察,诗歌具有了较多的哲思与深沉的品格。他似乎有着永不枯竭的精力与才情,于高负荷的工作之外,见缝插针,通宵达旦地写诗。这个时期的刘敏,工作繁忙,激扬高蹈,张开热情的怀抱,正在欣欣然拥抱多姿多彩的世界。
为了继续攀登诗歌圣殿,大约是在2016年前后,已经基本确立了小城文坛地位的刘敏,加入了都市圈诗歌群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姿态调整之后,很快地,他就适应了都市圈诗歌群体的环境,大踏步地追赶了上来;而且,以其勤奋与高产,迅速站稳了脚跟。
刘敏近年来所创作的诗歌,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给我。我只要有时间,会及时向他反馈。我们都对文学怀抱信仰与虔诚。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也常常直抒胸臆、不遮不掩、有一说一,肯定优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似乎也很在意我的评价。从前,我以为刘敏是坚定的、果敢的、自信的、骄傲的。这次读到他的诗歌集,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也不完整。我发现作为诗人的刘敏,非常敏感、多情、脆弱,他无数次地、孜孜不倦地、经年累月地反复回忆故乡、母亲、父亲,对儿时的饥饿、孤独、贫穷、无助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记忆。每每读到他的这些诗句与文字,我总会感同身受、眼含热泪、心情沉重。这与我无数次见到的作为一位顶天立地、倜傥风流、热情似火、疾恶如仇、慷慨大方、助人为乐、广结善缘、横槊赋诗、辞章锦绣的刘敏,简直判若两人。
刘敏的这部诗稿题材广泛、形式新巧、风格多变,从中可以窥见他近年来在“有意为诗”的专业化道路上不懈探索与勉力实践的勃勃雄心与用力之勤、成果之丰。作为对刘敏诗歌创作个案的分析,2017年8月,我曾对他的诗歌《祖屋》进行研究,并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他的创作全貌与风格流变脉络进行概要梳理。该文深得刘敏肯定与信任。同样地,在这部诗稿中,除了吟咏土地与怀念母亲的那些勾起我们情感共鸣的诗作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写一辈子郁郁不得志、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心境自由、逆境中不甘沉沦、身残志坚、向往光明、扎根穷乡僻壤、躬耕三尺讲台、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乐观旷达、向上向善的故乡的农夫、盲人、乡村教师、贩夫走卒、市井小民、老街生意人、闾巷手艺人……这类诗作,书写的都是我们身边平凡而普通的老百姓,用语平实、语调平缓,在几乎是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讲述他们生活的不易、生计的艰难、平凡的伟大、闪光的心灵、小草一样的坚韧,读来无不触动心弦、眼眶模糊——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敏诗歌所掬捧的这些涓涓溪流,早已融入了我们这个泱泱古国千年流淌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河流,这就是——为着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人民而书写与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