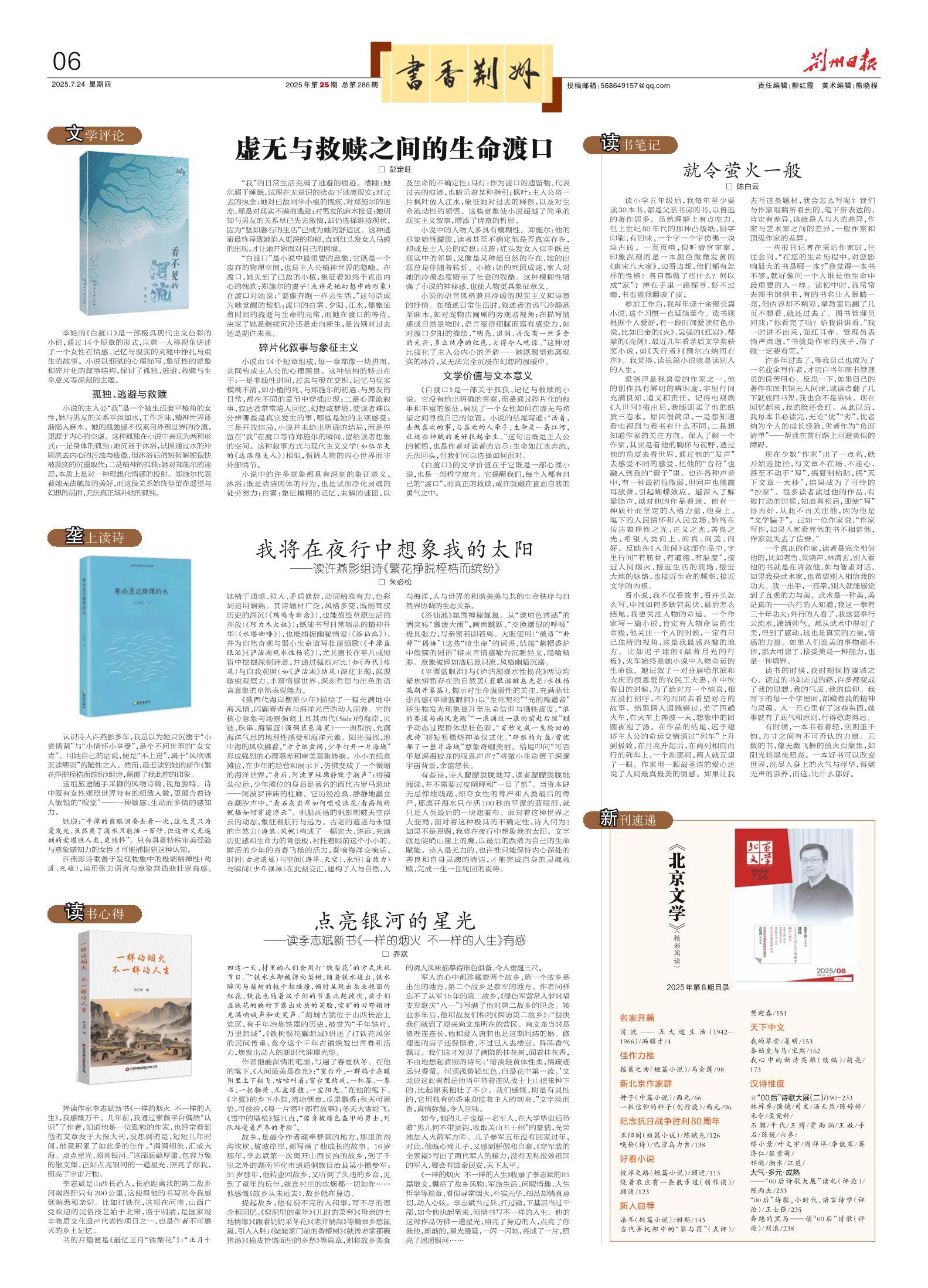□ 陈白云
读小学五年级后,我每年至少要读30本书,都是父亲书房的书,以鲁迅的著作居多。虽然理解上有点吃力,但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凸版纸,铅字印刷,有旧味,一个字一个字仿佛一块块古砖。一页页啃,似听清官审案。印象深刻的是一本颜色微微发黄的《唐宋八大家》,边看边想,他们都有怎样的性格? 各自都做了些什么? 何以成“家”? 捧在手里一路探寻,好不过瘾,书也被我翻破了皮。
参加工作后,我每年读十余部长篇小说,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选书则根据个人爱好,有一段时间爱读红色小说,比如巴金的《火》、吴强的《红岩》、都梁的《亮剑》,最近几年看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如《天行者》《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觉得,读长篇小说就是读别人的人生。
梁晓声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字里行间充满良知、道义和责任。记得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后,我随即买了他的纸质三卷本。原因很简单,一是想知道看电视剧与看书有什么不同,二是想知道作家的关注方向。深入了解一个作家,其实是看他的胸怀与视野,透过他的角度去看世界,通过他的“发声”去感受不同的感受,把他的“音符”也融入到我的“谱子”里。也许各种声音中,有一种最初很微弱,但回声也能震耳欲聋,引起蝴蝶效应。越深入了解梁晓声,越对他的作品着迷。他有一种质朴而坚定的人格力量,他身上、笔下的人民情怀和人民立场,始终在传达着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希望人类向上、向真、向美、向好。反映在《人世间》这部作品中,字里行间“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接近人间烟火,接近生活的现场,接近大地的脉络,也接近生命的频率,接近文学的内核。
看小说,我不仅看故事,看开头怎么写、中间如何多跌宕起伏、最后怎么结尾,我更关注人物的命运。一个作家写一篇小说,肯定有人物命运的生命线,他关注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火车始终是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生命线。她记叙了一对分居哈尔滨和大庆的很恩爱的农民工夫妻,在中秋假日的时候,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相互没打招呼,不约而同去看望对方的故事。结果俩人遗憾错过,坐了四趟火车,在火车上奔波一天,想象中的团圆夜泡了汤。在作品的结尾,迟子建将主人公的命运交错通过“列车”上升到极致,在月亮升起后,在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上,一个刹那间,两人就互望了一眼。作家用一颗最圣洁的爱心述说了人间最真最美的情感。如果让我去写这类题材,我会怎么写呢? 我们与作家眼睛所看到的、笔下所表达的,肯定有差异,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异,作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差异,一般作家和顶级作家的差异。
一些报刊记者在采访作家时,往往会问,“在您的生命历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一本?”我觉得一本书不够,就好像问一个人谁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样。读初中时,我常常去图书馆借书,有的书名让人眼睛一亮,但内容却不精彩,拿教室后翻了几页不想看,就还过去了。图书管理员问我:“你看完了吗? 给我讲讲看。”我一时讲不出来,面红耳赤。管理员表情严肃道,“书就是作家的孩子,借了就一定要看完。”
许多年过去了,等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业余写作者,才明白当年图书管理员的良苦用心。反思一下,如果自己的著作在图书馆无人问津,或读者翻了几下就放回书架,我也会不是滋味。现在回忆起来,我的脸还会红。从此以后,我每本书必读完,无论“优”“劣”,优者纳为个人的成长经验,劣者作为“负面清单”——帮我在前行路上回避类似的障碍。
现在少数“作家”出了一点名,就开始走捷径,写文章不在场、不走心,甚至不动手“写”,搞复制粘贴,搞“天下文章一大抄”,结果成为了可怜的“抄家”。很多读者读过他的作品,有被打动的时候,知道真相后,即使“写”得再好,从此不再关注他,因为他是“文学骗子”。正如一位作家说,“作家写作,如果人家看完他的书不相信他,作家就失去了信誉。”
一个真正的作家,读者是完全相信他的,比如老舍、梁晓声、林清玄,别人看他的书就是在请教他,如与智者对话。如果我是武术家,也希望别人相信我的功夫。我一出手,一亮拳,别人就能感觉到了直观的力与美。武术是一种美,美是真的——内行的人知道,我这一拳有三十年功夫;外行的人看了,我这套拳行云流水,潇洒帅气。都从武术中得到了美,得到了感动,这也是真实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如果人们连美的事物都不信,那太可悲了,接受美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境界。
读书的时候,我时刻保持虔诚之心。读过的书如走过的路,许多都变成了我的思想、我的气质、我的信仰。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里面,都藏着我的精神与灵魂。人一旦心里有了这些东西,做事就有了底气和原则,行得稳走得远。
有时候,一本书看着轻,实则重千钧,方寸之间有不可否认的力量。无数的书,像无数飞舞的萤火虫聚集,如阳光将黑夜照亮。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世界,洗尽人身上的火气与浮华,得到无声的滋养,而这,比什么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