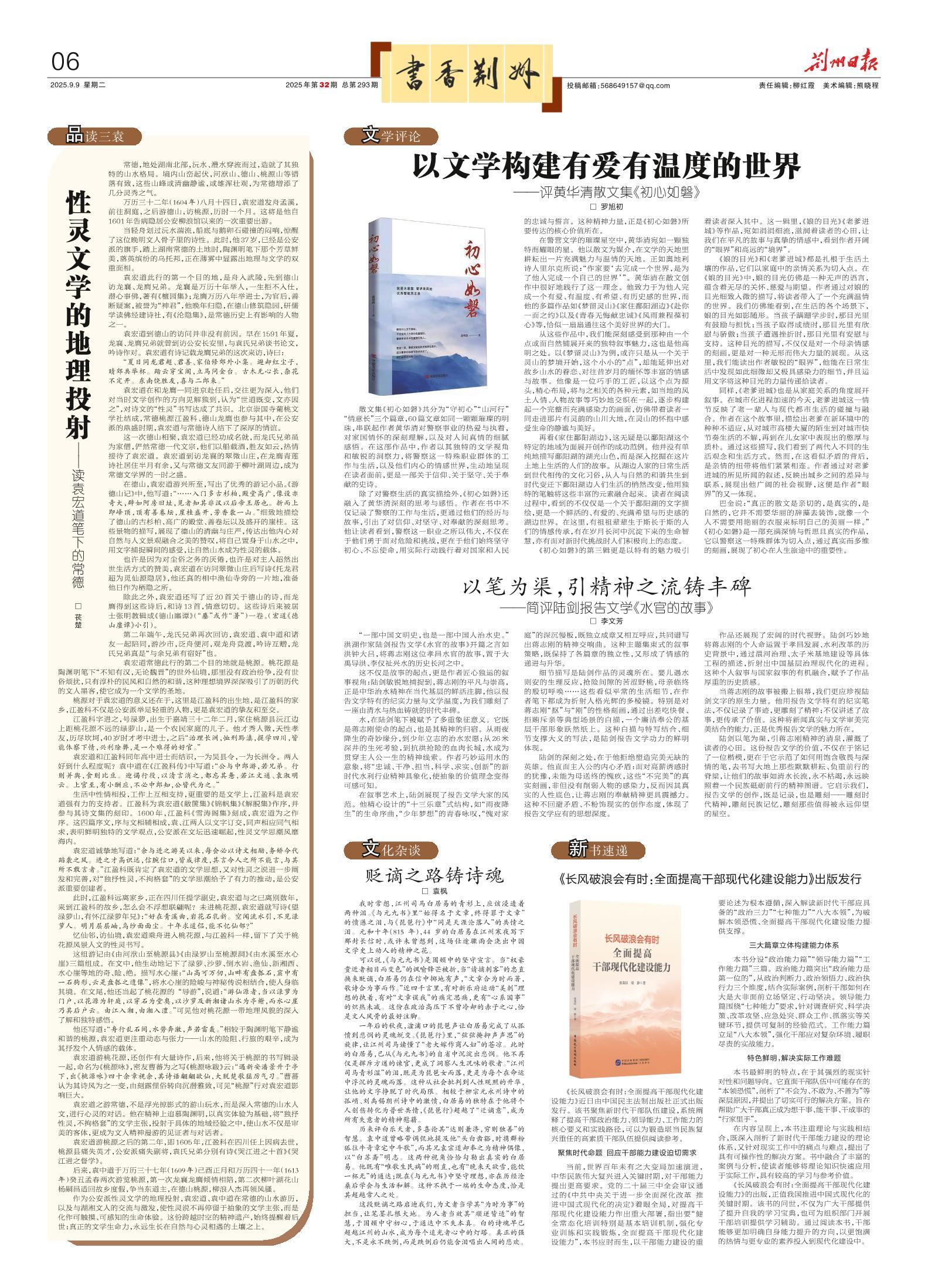□ 袁枫
我时常想,江州司马白居易的青衫上,应该浸透着两种泪。《与元九书》里“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的愤懑之泪,与《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之泪。元和十年(815年),44岁的白居易在江州寒夜写下那封长信时,或许未曾想到,这场仕途骤雨会浇出中国文学史上动人的精神之花。
可以说,《与元九书》是困顿中的坚守宣言。当“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的讽喻锋芒被折,当“请捕刺客”的忠直换来贬谪,白居易仍在信中掷地有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近四千言里,有对新乐府运动“美刺”理想的执着,有对“文章误我”的痛定思痛,更有“心系国事”的炽热未减。这份在政治高压下不曾冷却的赤子之心,恰是文人风骨的最好注脚。
一年后的秋夜,湓浦口的琵琶声让白居易完成了从孤愤到悲悯的灵魂蜕变。《琵琶行》里,“弦弦掩抑声声思”的旋律,让江州司马读懂了“老大嫁作商人妇”的苍凉。此时的白居易,已从《与元九书》的自省中沉淀出悲悯。他不再仅是挥斥方遒的谏官,更成了洞察人生况味的歌者。“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泪,既是为琵琶女而落,更是为每个在命运中浮沉的灵魂而落。这种从社会批判到人性观照的升华,让他的文字挣脱了时代局限。相较于柳宗元永州诗中的孤峭、刘禹锡朗州诗中的激愤,白居易的独特在于他将个人创伤转化为普世共情,《琵琶行》超越了“迁谪意”,成为所有失意者的精神慰藉。
历来评白乐天者,多喜论其“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智慧。袁中道曾略带调侃地提及他“头白齿豁,时携群粉狐往牛奇章宅中斗歌”,而其兄袁宗道却奉之为精神偶像,以“白苏斋”明志。这两种视角恰恰勾勒出真实的白居易。他既有“唯歌生民病”的刚直,也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通达;既在《与元九书》中坚守理想,亦在历经沧桑后学会与生活和解。这种不执于一端的生命态度,恰是其超越常人之处。
这段贬谪之路启迪我们,为文者当学其“为时为事”的担当,让笔墨扎根大地。为人者当效其“顺逆皆适”的智慧,于困顿中守初心,于通达中不失本真。白的诗魂早已超越江州的山水,成为每个追光者心中的灯塔。真正的强大,不是永不跌倒,而是跌倒后仍能含泪唱出人间的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