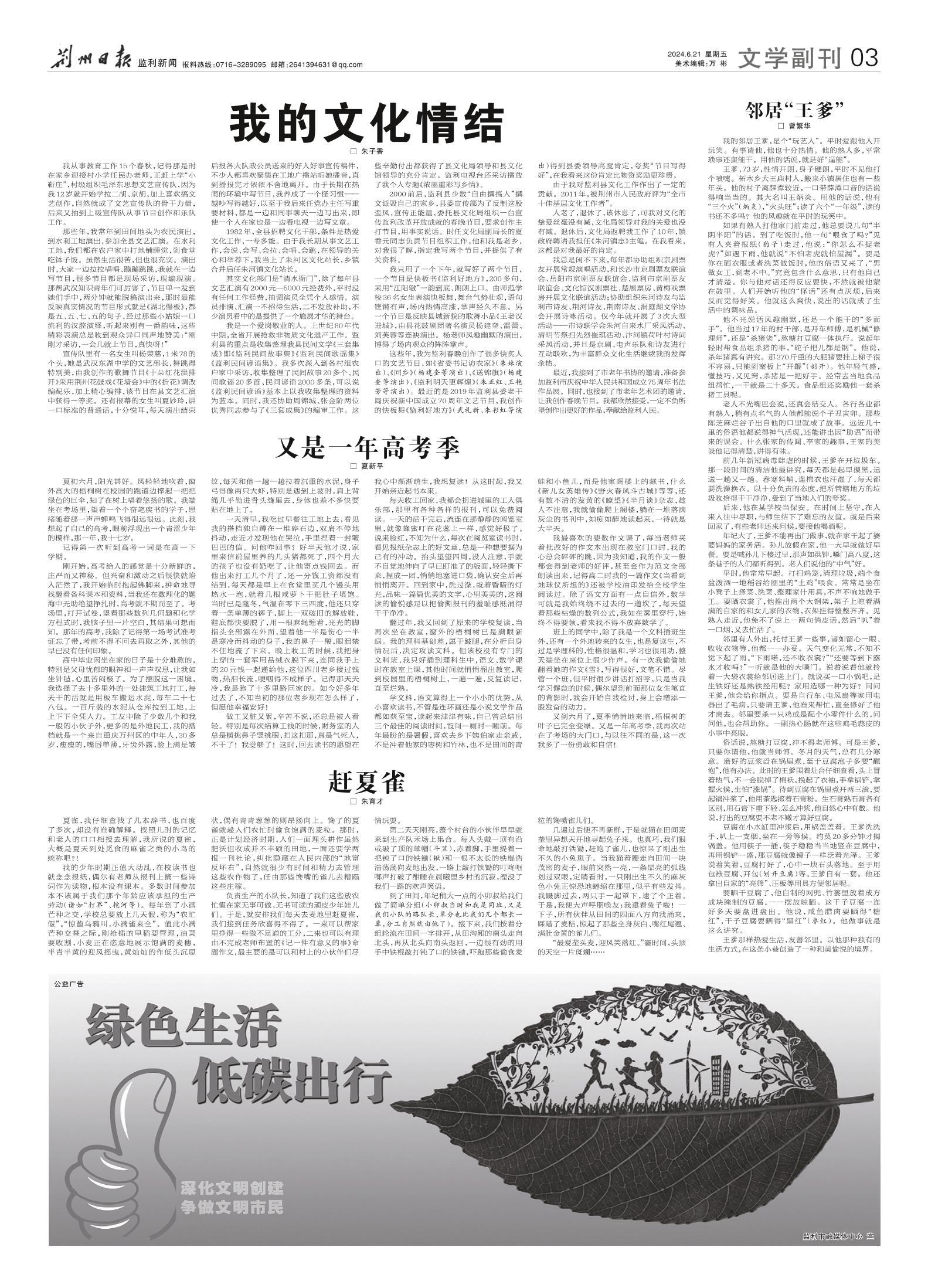□ 曾繁华
我的邻居王爹,是个“玩艺人”。平时爱跟他人开玩笑。有事请他,他也十分热情。他的熟人多,平常琐事还蛮能干。用他的话说,就是好“逞能”。
王爹,73岁,性情开朗,身子硬朗,平时不见他打个喷嚏。柘木乡大王庙村人,搬来小镇居住也有一些年头。他的村子离薛潭较近,一口带薛潭口音的话说得响当当的。其大名叫王炳炎。用他的话说,他有“三个火”(炳炎),“火头旺”;读了六个“一年级”,读的书还不多吗? 他的风趣就在平时的玩笑中。
如果有熟人打他家门前走过,他总要说几句“半阴半阳”的话。到了吃饭时,他一句“喂食了吗?”见有人夹着报纸(豹子)走过,他说:“你怎么不捉老虎?”如遇下雨,他就说“不怕老虎就怕屋漏”。要是你在晒衣服或者洗菜做饭时,他的俗语又来了,“男做女工,到老不中。”究竟包含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你与他对话还得反应要快,不然就被他蒙在鼓里。人们开始听他的“怪话”还有点厌烦,后来反而觉得好笑。他就这么爽快,说出的话就成了生活中的调味品。
他不光说话风趣幽默,还是一个能干的“多面手”。他当过17年的村干部,是开车师傅,是机械“修理师”,还是“杀猪佬”,熬糖打豆腐一体执行。说起年轻时帮食品组杀猪的事,“砣子把儿都是钢”。他说,杀年猪真有讲究。那370斤重的大肥猪要挂上梯子很不容易,只能到案板上“开鞭”(剖开)。他年轻气盛,懂技巧,又见窍,杀猪是一把好手。经常去当地食品组帮忙,一干就是二十多天。食品组还奖励他一套杀猪工具呢。
老人不光嘴巴会说,还真会结交人。各行各业都有熟人,稍有点名气的人他都能说个子丑寅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出自他的口里就成了故事。远近几十里的俗语他都说得神气活现,还能讲出因“助语”而带来的误会。什么张家的传闻、李家的趣事、王家的美谈他记得清楚,讲得有味。
前几年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王爹在开垃圾车。那一段时间的清洁他最讲究,每天都是起早摸黑,运送一趟又一趟。春寒料峭,连棉衣也汗湿了,每天都要洗澡换衣。以十分负责的态度,把所管辖地方的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受到了当地人们的夸奖。
后来,他在某学校当保安。在时间上坚守,在人来人往中尽职,与师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就是后来回家了,有些老师还来问候,要接他喝酒呢。
年纪大了,王爹不能再出门做事,就在家干起了婆婆妈妈的家务活。孙儿放假在家,他一大早就做好早餐。要是喊孙儿下楼过早,那声如洪钟,嗓门高八度,这条巷子的人们都听得到。老人们说他的“中气”好。
平时,他常常早起。打扫鸡笼,清理垃圾,端个食盆泼洒一地稻谷给圈里的“土鸡”喂食。常常是坐在小凳子上择菜、洗菜、整理家什用具,不声不响地做手工。要晒衣裳了,他推出两个大钢架,架子上晾着满满的自家的和女儿家的衣物,衣架挂得整整齐齐。见熟人走近,他免不了说上一两句俏皮话,然后“叭”着一口烟,又去忙活了。
邻里有人外出,托付王爹一些事,诸如留心一眼、收收衣物等,他都一一办妥。天气变化无常,不知不觉下起了雨。“下雨喏,还不收衣裳?”“还要等到下露水才收吗?”一听就是他的大嗓门。说着说着他就拎着一大袋衣裳给邻居送上门。就说买一口小锅吧,是生铁好还是熟铁经用呢? 家用选哪一种为好? 问问王爹,他会给你指点。要是自行车、电风扇等家用电器出了毛病,只要请王爹,他准来帮忙,直至修好了他才离去。邻里要杀一只鸡或是配个小零件什么的,问问他,也会帮助你。一副热心肠就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亮眼。
俗话说,熬糖打豆腐,冲不得老师傅。可是王爹,只要你请他,他就当师傅。冬月的天气,总有几分寒意。磨好的豆浆舀在锅里煮,至于豆腐泡子多要“醒泡”,他有办法。此时的王爹围着灶台仔细查看,头上冒着热气,不一会脱掉了棉袄,挽起了衣袖,手拿锅铲,掌握火候,生怕“涨锅”。待到豆腐在锅里煮开两三滚,要起锅冲浆了,他用茶匙搲着石膏粉。生石膏熟石膏各有区别,用石膏下重下轻、怎么冲浆,他自然心中有数。他说,打出的豆腐要不老不嫩才算好豆腐。
豆腐在小水缸里冲浆后,用锅盖盖着。王爹洗洗手,叭上一支烟,坐在一旁等候。约莫20多分钟才揭锅盖。他用筷子一插,筷子稳稳当当地竖在豆腐中,再用锅铲一盛,那豆腐就像镜子一样泛着光泽。王爹说着笑着,豆腐打好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至于用包袱豆腐、开包(划开豆腐)等,王爹自有一套。他还拿出自家的“亮筛”、压板等用具方便邻居呢。
要晒干豆腐了,他自制的网兜、竹篓里放着成方成块腌制的豆腐,一一摆放晾晒。这干子豆腐一连好多天要盘进盘出。他说,咸鱼腊肉要晒得“糖红”,干子豆腐要晒得“黑红”(枣红)。他做事就是这么讲究。
王爹那样热爱生活,友善邻里。以他那种独有的生活方式,在这条小巷创造了一种和美愉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