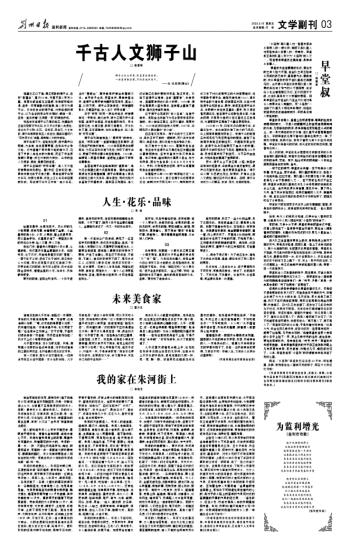|
||||
|
□彭桂生 每当那首悠扬悦耳、甜美动听《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曲在我耳畔回荡,仿佛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也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家乡。是啊!最美家乡水,最亲朱河人。我的家乡朱河南连长江、东襟洪湖,通江达湖,是一座历史久远,文化灿烂,贸易发达、美丽富饶的商业古镇,享有“小汉口”“金朱河”美誉而闻名遐迩。 世人都知道朱河人心灵手巧嘴巴乖,精明能干把你卖。滑稽尖当有板眼,能说会道心不坏。我是听着朱河街上的故事、喝着朱家河里的水、数着青石板长大的。朱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我魂牵梦绕,痴迷、钟情和留恋,那里的一点一滴都能勾起我最美好、最甜蜜的回忆。家乡究竟有哪些迷人和向往的地方呢?那就容我这个纯粹的朱河佬来敲一敲、咵一咵。 朱河的街道最迷人。朱河自宋朝立埠,至清乾隆年间“商民辐辏,最称繁盛”。朱河初名芦陵河,源于明末万历年间的一位同名朱河老人,河因人名,人依河兴,街傍河旺。一条河成就了一条街,七里长的青石板街好似一条蜿蜒巨龙,龙首是老人仓,龙尾是鹿苑庵。龙身两侧是古朴的明清木楼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排列着350多家店铺,其中药铺就有30多家。青砖燕瓦的屋檐下可遮荫避雨。贯穿河街的大小民巷有20多个,其中有吴家巷、刘家巷、祠巷子、土地巷、杨巷子等,上街下河既方便又畅通。雨后木屐声、天明车轮声、白天吆喝声、还有晚上打更(铜锣)声,不绝于耳,汇成一曲小镇闹市的交响乐。儿时在清澈见底的河里淘米洗菜打刨囚、挑水浆衣打水漂,玩得尽兴。最吸引我的还是刘巷子说书的、吴巷子买书的、罗巷子租书的,还有上街头的电影院和戏院子,都是我的好去处。当时朱河的镇办厂星罗棋布,如电线厂、自行车配件厂、纺织厂、机耕船厂、粉末冶金厂、黄麻经纺厂、猎枪厂、皮革社等等几十家,红红火火,居民安居乐业,社会祥和安宁。 朱河的方言最逗人。朱河人的语音高、语速快;嗓门大、喉咙粗。朱河人走南闯北,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但乡音未改,舌头伸不直,土得掉渣,让人即懂非懂。但不腔作势,不假嘎马嘎,而是贴近生活,地方特色浓郁。朱河人性格耿直,刀子嘴、豆腐心,说话直来直去,不转弯抹角,可以做“梗朋友”。朱河民风淳朴,同屋邻里耳鬓厮磨,声息相通。我的家就在祠巷子下首河正岸邹正顺(原为布店)的私宅里(已改造为公房),庭院曲深,一个屋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在这深幽老宅里玩游戏、躲枪蒙(意为捉迷藏)、攻学业,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人们在对话中不时会冒出几句粗话、荤话和抽筋的话。常说的是:搞母家?见人就问:吃饭嘛?口头禅是:三夾一入(夾屁、夾卵、夾鸡巴;入假子的)。还有地道的俚语土话,如焦同吊子瓢,憨吃哈胀、流皮痒身、斜骗话脸、戳皮打拐、乌七八公、黄尼希胡、扯白练谎、摊尸、刮气、线车、敲期、冈山、胀禄、茅室、一哈儿、撮打拐、打条胯、贱三爷、入哈三、逗西壳等等,诙谐幽默,非常有趣,总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真的是:路隔十里,乡音不同。 朱河的美食最馋人。朱河人不但好吃,而且会做,非常讲究厨艺。烹蒸煎炸炒、煮燉煲烩卤,色香味形俱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令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如进贡给慈禧太后品尝过的吉祥如意龙凤喜饼(流糖饼)、味甜香浓的叠汤丸、鲜嫩可口的生炸豆腐丸、外焦内软的灯草窝、糖心藕丸子、排骨莲藕汤,还有那凉面、包面和热干面,三蒸四糕(蒸鱼、蒸肉、蒸丸子;蒸糕、挖糕、顶糕、炕糕)更诱人。尤其是吴家巷的锅块;一桥何老板的团子、米粑子;刘巷子朱府的卤千张、卤蓑衣干子、卤肠子和猪耳朵;更有下街王矮爹的包面等,各具特色,应有尽有,热腾腾、香喷喷、麻辣辣、嫩滑滑,吃了还想吃。早酒店人声鼎沸,夜市摊通宵达旦,到处弥漫着烟火气、散酒味,食客们开怀畅饮,高谈阔论,牛气冲天。 朱河的夜晚最撩人。夏夜纳凉,朱河街道两旁热闹异常。每当夜幕降临,繁星闪烁,万家灯火,炊烟袅袅,人们开始升火做饭,只听见锅碗瓢盆和小孩嬉戏声。待洗刷完毕,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才开始歇息。家家户户,各自在家门前、街道边、屋檐下准备过夜的行当,先是洒一遍水降温压尘后,再用床板竹席搭凉铺、摆竹床。一条街首尾相连,横七竖八,连绵不绝,铺天盖地,煞是壮观。大人小孩,全都无遮无挡,仰卧咵野白、摆龙门阵;抬头数星星、讲鬼故事,无拘无束,随心所欲,野性十足。有的大人吃宵夜、打平火,袒胸露背,赤膊上阵、摇芭扇、喝烧酒,划拳猜令,谈笑风生,唾沫四飞,引得路人纷紛驻足观看,并成为朱河街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时大门敞开,人们进出自如,毫不设防,一觉睡到天大亮,无须防盗防贼防拐卖。真是个道不失遗、门不闭户的清平安乐世界。 朱河的人物最感人。朱河文化底蕴深厚,文人墨客灿若繁星。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出了安邦定国的将帅、辅佐君主的重臣、清正廉明的官吏、诲人不倦的名师等先贤俊杰。古有清代山西布政史胡大任、太平军左路统领秦光明、台湾知府朱材哲等;今有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琪、中共湘鄂边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董达三等、战斗英雄王逸夫;名商巨贾黄少山、沈万山在此发迹。政坛商界、文苑社团,人才济济,名扬海内外。著书立说者更不计其数,我收藏的著书就有几十部,既有诙谐幽默的小说、也有清新明快的散文、还有旧律新韵的诗集、更有神奇式的传记与纪实文学,如珠似玉,璀璨夺目。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朱河中学初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乡下放到渔场,尔后进城调到县直行政管理机关工作。五十多年来,我经常回家看望父母、探亲访友、重返母校、参加活动、重温旧梦。对家乡无时不怀有深厚而炽烈的情感,上世纪80年代我曾下派到朱河镇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局机关退休后,不断用心用情用笔,撰写和发表文章宣传赞美家乡。为什么我常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人和事,有那亲切的乡音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还有我那童年和少年时的影子和足迹。正如著名诗人艾青写道:“当黄昏时走在田野上,那如此不可排遣地困惑着我的心的,是对于故乡路上的畜粪的气息和村边的畜棚里的干草的气息的记忆啊……”留恋故乡、记住乡愁、热爱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和守望。此刻,我要将《谁不说俺家乡好》中的一句歌词奉献并祝福我的家乡人民:“幸福生活千年万年长!” (作者系监利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党员干部、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已出版个人文学专集《兰桂生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