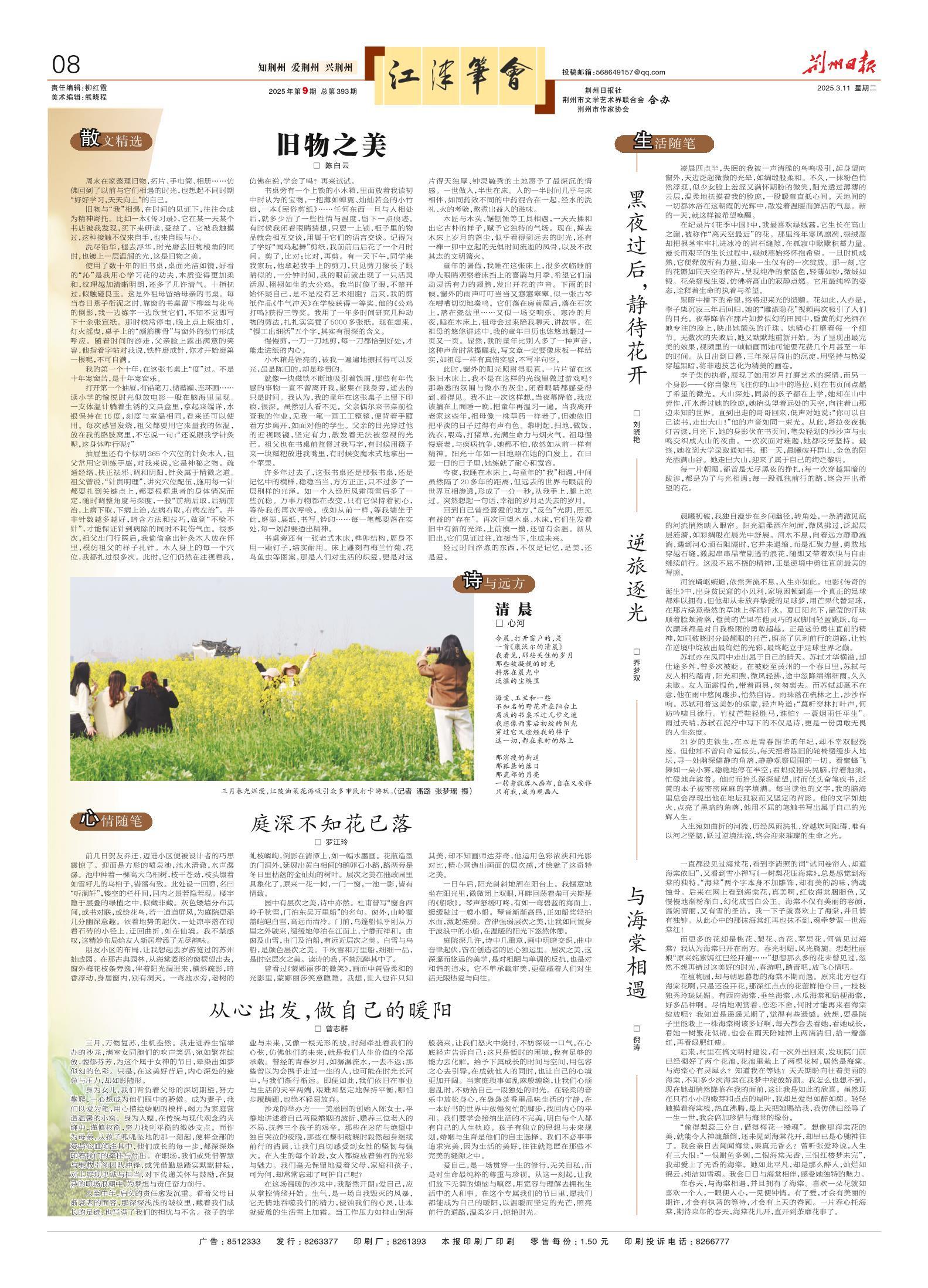□ 陈白云
周末在家整理旧物,拓片、手电筒、相册……仿佛回到了以前与它们相遇的时光,也想起不同时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自己。
旧物与“我”相遇,在时间的见证下,往往会成为精神寄托。比如一本《传习录》,它在某一天某个书店被我发现,买下来研读,受益了。它被我触摸过,这种接触不仅来自手,也来自眼与心。
洗尽铅华,褪去浮华,时光磨去旧物棱角的同时,也镀上一层温润的光,这是旧物之美。
使用了数十年的旧书桌,桌面光洁如镜,好看的“沁”是我用心学习花的功夫,木质变得更加柔和,纹理越加清晰明朗,还多了几许清气。十指抚过,似触碰良玉。这是外祖母留给母亲的书桌。每当春日燕子衔泥之时,靠窗的书桌留下柳丝与花鸟的倒影,我一边练字一边欣赏它们,不知不觉即写下十余张宣纸。那时候常停电,晚上点上煤油灯,灯火摇曳,桌子上的“颜筋柳骨”与窗外的劲竹形成呼应。随着时间的游走,父亲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指着字帖对我说,铁杵磨成针,你才开始磨第一根呢,不可自满。
我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张书桌上“度”过。不是十年寒窗苦,是十年寒窗乐。
打开第一个抽屉,有铅笔刀、储蓄罐、连环画……读小学的愉悦时光似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呈现。一支体温计躺着生锈的文具盒里,拿起来端详,水银保持在15度,刻度与室温相同,看来还可以使用。每次感冒发烧,祖父都要用它来量我的体温,放在我的胳肢窝里,不忘说一句:“还说跟我学针灸呢,这身体咋行呢?”
抽屉里还有个标明365个穴位的针灸木人,祖父常用它训练手感,对我来说,它是神秘之物。疏通经络、扶正祛邪、调和阴阳,针灸属于精微之道。祖父曾说,“针贵明理”,讲究穴位配伍,施用每一针都要扎到关键点上,都要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而定,随时调整角度与深度,一般“前病后取,后病前治,上病下取,下病上治,左病右取,右病左治”。并非针数越多越好,暗含方法和技巧,做到“不验不针”,才能保证针到病除的同时不耗伤气血。很多次,祖父出门行医后,我偷偷拿出针灸木人放在怀里,模仿祖父的样子扎针。木人身上的每一个穴位,我都扎过很多次。此时,它们仍然在注视着我,仿佛在说,学会了吗? 再来试试。
书桌旁有一个上锁的小木箱,里面放着我读初中时认为的宝物,一把薄如蝉翼、灿灿若金的小竹扇,一本《民俗剪纸》……任何东西一旦与人相处后,就多少沾了一些性情与温度,留下一点痕迹。有时候我闭着眼睛猜想,只要一上锁,柜子里的物品就会相互交谈,用属于它们的语言交谈。记得为了学好“闻鸡起舞”剪纸,我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剪了,比对;比对,再剪。有一天下午,同学来我家玩,他拿起我手上的剪刀,只见剪刀像长了眼睛似的,一分钟时间,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大公鸡。我当时傻了眼,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艺术细胞? 后来,我的剪纸作品《牛气冲天》在学校获得一等奖,他的《公鸡打鸣》获得三等奖。我用了一年多时间研究几种动物的剪法,扎扎实实费了5000多张纸。现在想来,“慢工出细活”五个字,其实有很深的含义。
慢慢剪,一刀一刀地剪,每一刀都恰到好处,才能走进纸的内心。
小木箱是锃亮的,被我一遍遍地擦拭得可以反光,虽是陈旧的,却是珍贵的。
就像一块磁铁不断地吸引着铁屑,那些有年代感的事物一直不曾离开我,聚集在我身旁,逝去的只是时间。我认为,我的童年在这张桌子上留下印痕,很深。虽然别人看不见。父亲偶尔来书桌前检查我的作业,见我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便背着手踱着方步离开,如面对他的学生。父亲的目光穿过他的近视眼镜,坚定有力,散发着无法被忽视的光芒。祖父也在书桌前监督过我写字,有时候用筷子夹一块糍粑放进我嘴里,有时候变魔术式地拿出一个苹果。
许多年过去了,这张书桌还是那张书桌,还是记忆中的模样,稳稳当当,方方正正,只不过多了一层别样的光泽。如一个人经历风霜雨雪后多了一些沉稳。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只有它保持着初心,等待我的再次呼唤。或如从前一样,等我端坐于此,磨墨、展纸、书写、钤印……每一笔都要落在实处,每一划都要透出精神。
书桌旁还有一张老式木床,榫卯结构,周身不用一颗钉子,结实耐用。床上雕刻有梅兰竹菊、花鸟鱼虫等图案,那是人们对生活的炽爱,更是对这片得天独厚、钟灵毓秀的土地寄予了最深沉的情感。一世做人,半世在床。人的一半时间几乎与床相伴,如同药效不同的中药混合在一起,经水的洗礼、火的考验,熬煮出益人的滋味。
木匠与木头、锯刨锤等工具相遇,一天天揉和出它古朴的样子,赋予它独特的气场。现在,掸去木床上岁月的落尘,似乎看得到远去的时光,还有一榫一卯中立起的无惧时间流逝的风骨,以及不改其志的文明篝火。
童年的暑假,我睡在这张床上,很多次临睡前睁大眼睛观察着床挡上的喜鹊与月季,希望它们扇动灵活有力的翅膀,发出开花的声音。下雨的时候,窗外的雨声叮叮当当又窸窸窣窣,似一张古琴在嘈嘈切切地奏鸣。它们落在房前屋后,落在石坎上,落在瓷盆里……又似一场交响乐。寒冷的月夜,睡在木床上,祖母会过来陪我聊天、讲故事。在祖母的悠悠讲述中,我的童年日历也悠悠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显然,我的童年比别人多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时常提醒我,写文章一定要像床板一样结实,如祖母一样有真情实感,不写半句空。
此时,窗外的阳光照射得很直,一片片留在这张旧木床上,我不是在这样的光线里做过游戏吗?那熟悉的氛围与微小的灰尘,闭着眼睛都感受得到、看得见。我不止一次这样想,当夜幕降临,我应该躺在上面睡一晚,把童年再温习一遍。当我离开老家这些年,祖母像一株草药一样老了,但她依旧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黎明起,扫地,做饭,洗衣,喂鸡,打猪草,充满生命力与烟火气。祖母慢慢衰老,与疾病抗争,她都不怕,依然如从前一样有精神。阳光十年如一日地照在她的白发上。在日复一日的日子里,她练就了耐心和宽容。
今夜,我睡在木床上,与童年的“我”相遇,中间虽然隔了20多年的距离,但远去的世界与眼前的世界互相渗透,形成了一分一秒,从我手上、腿上流过。突然想起一句话,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
回到自己曾经喜爱的地方,“反刍”光阴,照见有益的“存在”。再次回望木桌、木床,它们生发着旧中有新的光泽,上前摸一摸,还留有余温。新从旧出,它们见证过往,连接当下,生成未来。
经过时间淬炼的东西,不仅是记忆,是美,还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