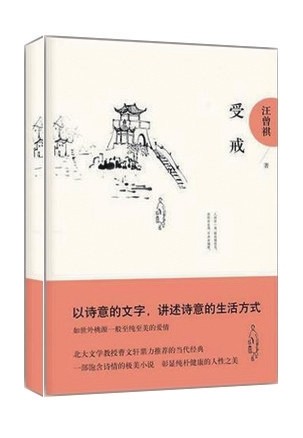□ 胡维
夜深人静时,我总爱翻翻书籍,最近翻阅的是汪曾祺的《受戒》,其中小和尚明海跟着舅舅学打鱼的情节,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水库上游抓鱼的往事。
里面的《羊舍一夕》和《小学校的钟声》更有意思。前者写四个孩子的夜话,又让我想起少年读书时和好友彻夜长谈的日子。虽然如今各奔东西,可那些时光就像河底的鹅卵石,被记忆的流水冲刷得越来越圆润光亮。后者写的自由,思绪飘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却最是贴近少年时的心思——天马行空,没个章法,可偏偏最是真挚。
我挺佩服他笔下把那些渔事写得极妙:“一网下去,白花花的一片,鲫鱼、鲤鱼、鲢鱼,还有叫不上名的小杂鱼。”我也见过岭南水乡的打鱼场景,但我们北方的河汊沟渠里水库边,却有我们孩子们独特的捕鱼方法。
高中时去到市里读书,最盼暑假回唐湾村老家。村东头那条河如今成为景点的那最精彩一段,便是我们的乐园。河水不深,清澈见底,阳光透过水面,在河底的鹅卵石上投下摇曳的光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常常赤着脚丫,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在浅滩处摸鱼。
最原始的法子是用手摸。双手轻轻探入水中,顺着石缝摸索。鲫鱼最是机灵,稍有动静便窜得无影无踪。倒是那些傻乎乎憨厚的泥鳅,常常躲在石缝里一动不动,被我们一把攥住。滑溜溜的身子在手心里扭动,痒得很,它这么滑溜,却又那么容易被捉住,倒是很奇怪。
后来不知谁发明了“竹笼子捕鱼法”。找个竹笼子广口的,笼口蒙上一块纱布,中间剪个小洞。笼子里放些猪肝、蚯蚓之类的,用绳子拴了沉入水中。不到一个小时提起来,笼子里准有一大堆贪嘴的小鱼在团团转。这法子虽只能捕到些柳条鱼、麦穗鱼之类的小杂鱼,却让我们乐此不疲。
每年暑假,刚好又是雨天,一夜暴雨后,河水就会微涨。我和堂弟、邻居家的一堆小伙伴们,就会用竹竿和蚊帐做了个简易的扳罾。沿着河岸一路慢慢扫荡。一个早上下来,都会收获丰盛,除了常见的鲫鱼、白条,还能网到一些金红色的鲤鱼。阳光下,鱼鳞闪烁着奇异的光彩,就像我们发着光一样的少年,洒脱、快乐。
如今想来,最有趣的倒不是捕鱼本身,而是那些准备工具的过程。削竹竿、编鱼笼、挖蚯蚓,每一样都充满创造的乐趣。有时为了做一个完美的工具,我会花整个下午挑选竹竿,打磨,直到符合我的标准。
窗外的月光洒在床前,我望着窗外的夜色,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时间的河流里捕捞着什么。而最珍贵的,或许永远是那些从指缝间溜走的瞬间。就像汪曾祺笔下那些平淡的渔事,看似随意道来,却藏着最深沉的人生况味。
汪老的文字,像极了江南的春雨,细细的,润润的,不知不觉就渗进心里去了。他写市井小民,写柴米油盐,写那些寻常巷陌里的悲欢,却总能在平淡处见真情,在苦难里留希望。读他的文字,就像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浑身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坦。
世人给汪曾祺的评价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话挺合适。